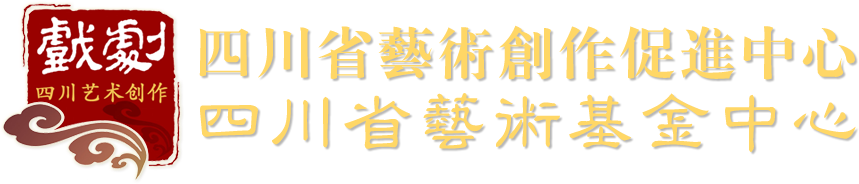
作者简介:周津菁:青年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戏剧家协会理事;现任重庆市文化研究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创作了舞台剧本《连木》《我的江湖》;川剧剧本《金染坊》《蛇妖小青》《聂小倩与宁采臣》,根据传统改编创作剧本《红梅记》《梁祝鸟》(与隆学义先生合作)。电影剧本《川江女号子头》获得重庆市第二届电影剧本征集评选活动提名作品奖;整理改编戏曲剧本《平叛招亲》获得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优秀改编剧目奖;原创舞台剧《连木》入围2015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单元前12强;创作“当代川剧”《聂小倩与宁采臣》获得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资助;原创川剧《金染坊》获得2017年度中国文联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资助;2018年参与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剧《金沙江畔》,该剧由四川省川剧院在第四届中国川剧节开幕式演出。学术方面,在各类核心期刊发表戏剧学论文10余篇,发表文艺评论50余篇。2016年公开出版专著《走向现代的川剧文学》,2017年公开出版专著《舞台环境下的现代川剧文学创作研究》
隆学义先生毕生创作了十余个戏剧作品,以女性形象作为主角的剧目占了多数,比如,川剧《金子》、川剧《鸣凤》、川剧《白露为霜》、川剧《貂蝉之死》、川剧《梦蝶》、京剧《江姐!江姐!》、方言话剧《河街茶馆》等剧。这些女性人物,所处的时代和人文环境各具特色,人物个性也有所不同,她们在不同戏剧剧目的各个差异性表达中,展示出了女性性格丰富性:忠烈、宽容、执着、纯真……这一次,重庆市三峡川剧团带着《白露为霜》来到第四届川剧节,借此机会,让我们来聊一聊隆老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塑造过程。
貂蝉、金子和鸣凤
“貂蝉”来自于戏曲作品《貂蝉之死》,是隆学义先生的早期作品。看过这个戏的观众对女主人翁貂蝉的“忠勇”和“刚烈”至今仍记忆犹新。川剧《貂蝉之死》共分为五场:“水淹下邳”“貂蝉休书”“关羽慕蝉”“群雄惊艳”“残月芳魂”。该剧以“三国演义”故事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的情节和人物为创作基础和戏剧文化背景,讲述了善良忠烈的貂蝉爱慕关羽厚德载物又豪放勇猛的英雄气概,却欲嫁之而不得,终而饮剑自尽的悲剧故事。传统折子戏“白门楼”在各地方戏中流布甚广,是一场艺术格调刚健硬朗的“男人戏”,充满了权术的火药味。隆学义独具匠心地将男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和心理角逐,化为了“群雄惊艳”貂蝉美色,而惊起的醋浪情波。曹操及刘、关、张等辈各自处于自己的立场,显示出了对“美女”微妙的反应。貂蝉就仿佛一面镜子,照射出男权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相互攻伐的激烈对抗性特征与“一团和气”障掩下的虚伪性。男性世界的“对抗与虚伪”和女性世界的“忠义、贞烈、纯洁”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貂蝉以纯洁的女性之思渴慕、向往着英雄,而英雄是男权社会的产物,美人在惊艳群雄之后,至多不过作为物品——正如剧作者设计的象征性符号:貂蝉手中的白玉连环,小小扇儿一样,作为群雄逐鹿的筹码被赠送。从貂蝉的角度来说,她修书给关羽以救下邳百姓的计策,足可见她的胆识和爱心,但男权社会并没有看到一个女子的剑胆琴心,她最终还是一个玩物。即使作为玩物,能嫁给大将军关羽,也是善终,但是刘玄德携张飞洞房赠礼,暗示“扶汉兴刘”的戏剧故事情节,把貂蝉最后的幸福希望全部带走了。既然羞了脸儿,罢了扇儿,嫁不得自己的心爱,受了屈辱的貂蝉选择了一个惨烈的死法,表达炽烈的情爱和执拗的忠诚。戏曲艺术形象的极端化处理,让这个人物熠熠生辉。
川剧《金子》始改编创作于1995年,由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担纲主演。初演时保存了曹禺原话剧剧名《原野》。这个从东北文化移植而来的故事,一开始便患上了川剧的不适应症。曹禺笔下的花金子,是一个参杂着野性和性欲的女人,这样的人物形象,川剧的旦角在她的面前显得过于“柔软”,因此川剧《原野》的第一次呈现对曹禺原著的表达就不准确。而创造一个“俏媳妇”金子形象,让川剧演“金子”的贴合度更高。这出川剧的名字因此由《原野》变为了《金子》。隆学义先生比理解一个东北少妇更加熟悉巴蜀媳妇儿,因此他笔下的金子具有巴蜀女人的特点“娇”“俏”“真”“直”“善”,在确立了人物的地方文化性格之后,隆学义着手改编情节桥段。而事实上,他发现传统川剧已经为她准备了大量的身法和程式,去帮助他呈现一个“娇”“俏”的富有地域风情的女人,这也正应了“艺术源于生活”一语。而隐藏在传统川剧旦角“俏丽”之下的,是一个个悲哀的灵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哪一个不是深居闺阁,备受束缚的女性形象,而川剧赋予了她们内敛、隐忍、幽怨的品格,即或是刚烈,也是在隐忍、凄丽的外套下表现,比如说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按照川剧表演的规律,一个美的金子,应该首先是丈夫的妻子,婆婆的媳妇,族弟的嫂嫂……她在表现她的独特个性之前,首先应该表现得温婉、隐忍、善良、规矩。她不能与自然天性对话,而只能与家庭关系对话;她不能讲欲望,而只能讲纯洁的感情——这是一个被传统戏曲样式所设计的,被伦理“极端束缚”的金子形象。此外,金子在舞台上又必须是美的,不能是野蛮的,应该是程式的,节制的,而不应该是轻狂的。善良风情的金子被卷入复仇的风潮之后,会有一个必然结果,那就是选择善良到底。女性本是世间真、善、美的代表,金子在作为第一主角之后,她的戏剧动机只会有一个:阻止虎子的复仇行为——她想跟虎子远走,去到黄金铺路的地方,了却仇虎心头的夺妻之恨;她想留住大星、焦母还有小黑子的性命,因为“冤冤相报何时了?”可是仇虎一心陷入复仇深渊而无法自拔。到这里,川剧《金子》的主题已经离话剧《原野》有距离了:《原野》讲述的是农民复仇的故事,戏剧主要冲突在仇虎与焦阎王寡妻焦母之间直接展开;而《金子》的矛盾中心在于“金子想要阻止仇虎复仇而不能”。阻止复仇,即倡导着以宽容去化解仇恨。宽容——这便是《金子》创新的戏剧主题。川剧《金子》声名远播,其原因并不是因为隆学义先生重复了曹禺,而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颇具巴蜀地域文化色彩的“金子”,并因为“金子”人物形象的成功,带动了整个剧作主题的升华。川剧《金子》中的“金子”形象,体现了“直率”“泼辣”“勇敢”的性格,而在表达过程中,由戏剧主题的深挖而带动的戏剧人物性格深度探索,让观众们懂得,“真诚”“善良”和“宽容”才是金子性格的真正内核。
川剧《鸣凤》改编自四川籍作家巴金小说《家》。这出戏由重庆市三峡川剧团演出,谭继琼因此剧摘取了第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这出戏主要讲述鸣凤追求自由爱情而不得,被封建主义毁灭的故事。鸣凤在巴金的《家》中只是一个“戏份”极少的小人物,她的生命如同萤火虫的光亮倏忽闪烁,最终消弭在阴沉的黑暗中。隆学义的川剧《鸣凤》拮取了萤火虫的意象,奠定了这出戏的唯美基调,并将此意象由歌、舞、说白等戏曲形式加以表现。创作立意点的奇特,使这出戏并不将“铺叙故事”作为叙事重点,而将笔力用于人物情感变化与跌宕的关节点上,该剧分为五场:“情绽”“爱鸣”“惊变”“敲窗”“投湖”。每一场戏的设计,都是为了生动淋漓地呈现一位少女——心灵的成长与挣扎。这种挣扎和成长实际上只基于“纯真”二字。川剧剧本《鸣凤》改编自巴金小说《家》。隆学义在《成都·巴金·<鸣凤>》中写道:“在《家》里,我对丫头鸣凤印象犹深。一朵荷花出水、一枝百合初开也似的少女,她的纯真被暴风撕碎,她的美好为淫雨毁灭。”(注:隆学义:《文心雕虫》,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第338页)如果说《牡丹亭》的杜丽娘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杜丽娘为爱可以超越生死,而遭受封建压迫的鸣凤,则只能投湖以谢真情。
陈白露背后的艰难创造
《白露为霜》改编自曹禺的另一部话剧作品《日出》。如陈白露一般的都市女性,无论是在故事发生的民国时期还是作者生活的当下,在都市环境中俯首皆是。而为了让巴蜀“陈白露”更具有地域特色,隆学义在剧中加入了巴蜀市井的民间环境,例如用四川清音《小放风筝》来表现少女时代的陈白露。陈白露善良,风情,又勇敢果断,有一场戏甚至写到她为救继女“小东西”出火坑,女扮男装深入狼穴,与男人争斗。而从本剧的主旨来看,隆学义对曹禺的“女性主题”进行了生发——更加深入地讨论了女人在现代社会的出路问题。陈白露身上被打上了当下都市女性的性格痕迹和命运困惑: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人皆渴慕幸福,而支撑幸福的到底应该是“物质”,还是“精神”和“自由的理想”?陈白露的精神世界正挣扎在这两种抉择之中:她走向社会,没能经受金钱和物质的诱惑,因此她又有沉沦的一面;而另一面,她心中仍然保持着对当年纯真情爱的眷恋,同时也在向金八这样的恶势力做斗争。隆学义发挥了戏曲写意的优越性,将曹禺《日出》中所蕴藏的象征主义意味进行了深刻开掘。“白露结清霜”的清曲反复吟诵,昭示着该剧的精神内涵:太阳出来了,霜就该化掉了——光明终将属于未来的人们,而丑恶和衰败的东西只能埋藏在过去。”陈白露从少女的清纯、善良发展到进入社会后的泼辣、沉沦,再到最后的觉醒和勇敢挣扎——抒写了一部女性性格成长史。隆学义正视了人类性格的复杂性,也同时抓住了重点,那就是巴蜀女性那份执着的探索意志和坚定的抗争精神。隆学义用戏剧的手法,为陈白露打上了地域文化的标签。
事实上,用戏曲的形式塑造陈白露的形象,是颇有难度的。在写作《金子》和《鸣凤》的时候,隆学义先生都采用了“一人一事”的戏曲叙事法,在立主脑,去枝蔓之后,全剧的人物关系和矛盾都围绕着主角金子和鸣凤旋转起来。而为了写活陈白露,编剧的叙事问题变得更加艰难起来。
2014年,著名文艺评论家马也先生两次在川剧《白露为霜》的研讨会上谈到:“将《日出》改编为戏曲几乎是不可能的。”(注:《隆学义戏剧艺术评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第158页。)话剧《雷雨》是写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悲剧,话剧《日出》则是在写一群人,写社会群体的悲剧式“狂欢”。
“因为要把实际生活中各有因果联系的人生悲剧集中在有限的舞台人物上,就必须使他们互为因果,构成彼此紧密联系的复杂网络。《雷雨》结构的高超处就在于此。但是,当《日出》的题材激动着曹禺的心的时候,《雷雨》的技巧马上使他感到不足甚至厌恶了。在这时,他仍然关心的是人,但却不仅仅是各个人物的命运,而是由这一个个人物构成的一种社会状态,一个完整的社会。要把一种社会状态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展现出来,也需要压缩和集中却不能让读者和观众明确地感觉出来。《日出》着眼的是社会世态的展现,因而它需要的不是每个人生命运的纵向发展过程,而主要是社会世态的展现。”(注:王富仁:《<日出>的结构和人物》,《曹禺研究1979-2009》,吉林文史出版社,第295页。)
话剧《日出》展示了十分广阔的社会画卷,人物复杂而众多,都围绕着“损不足以奉有余”一句话展开。虽然这个戏也称得上“形散而神聚”,而要把它改编成单纯的戏曲故事,还是颇有难度。隆学义先生面对的最直接问题就是,怎样用“一人一事”的口袋装下《日出》这个庞大的文学世界。这个戏为重庆市三峡川剧团的谭继琼而写,“陈白露”就是那个“一人”。而“一事”则难于解决了,本文作者暂且把这个话剧陈白露的故事描绘为:“纯洁的陈白露,本来有着健康的生活和爱情观念,而命运却让她进入尘世,在腐朽混乱的都市市井生活中堕落,渴求光明而不得。她难以抗拒绝望的折磨,终如白露为霜一般,融化在日出之后。”隆学义先生使用了传统文学中的诗话意象,来提纯曹禺原作错综的社会场景和人物故事,像川剧《金子》和《鸣凤》一样,希望让戏剧矛盾围绕主角而旋转。当矛盾繁多而难以贯穿时,他便创造性地以一首小诗贯穿全剧:“芦苇花飞白,白露结清霜。清霜如女郎,女郎绿水旁。日出清霜化,清心泥土藏。”说到底,话剧《日出》结构的松散,使得川剧《白露为霜》难于找到戏剧结构上的发力点。从曹禺提炼的“损不足以奉有余”,到隆学义提纯的“白露结清霜”,两个“日出”故事,都比具有完整情节和冲突的话剧《原野》、《雷雨》或川剧《金子》,具有更加浓重的诗话和象征意味,这是剧作家们在制造戏剧文学创作上的逻辑发力点。站在坚实的戏剧结构上,执着于光明的陈白露才得以立住!
作者简介:周津菁:青年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戏剧家协会理事;现任重庆市文化研究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创作了舞台剧本《连木》《我的江湖》;川剧剧本《金染坊》《蛇妖小青》《聂小倩与宁采臣》,根据传统改编创作剧本《红梅记》《梁祝鸟》(与隆学义先生合作)。电影剧本《川江女号子头》获得重庆市第二届电影剧本征集评选活动提名作品奖;整理改编戏曲剧本《平叛招亲》获得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优秀改编剧目奖;原创舞台剧《连木》入围2015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单元前12强;创作“当代川剧”《聂小倩与宁采臣》获得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资助;原创川剧《金染坊》获得2017年度中国文联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资助;2018年参与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剧《金沙江畔》,该剧由四川省川剧院在第四届中国川剧节开幕式演出。学术方面,在各类核心期刊发表戏剧学论文10余篇,发表文艺评论50余篇。2016年公开出版专著《走向现代的川剧文学》,2017年公开出版专著《舞台环境下的现代川剧文学创作研究》
隆学义先生毕生创作了十余个戏剧作品,以女性形象作为主角的剧目占了多数,比如,川剧《金子》、川剧《鸣凤》、川剧《白露为霜》、川剧《貂蝉之死》、川剧《梦蝶》、京剧《江姐!江姐!》、方言话剧《河街茶馆》等剧。这些女性人物,所处的时代和人文环境各具特色,人物个性也有所不同,她们在不同戏剧剧目的各个差异性表达中,展示出了女性性格丰富性:忠烈、宽容、执着、纯真……这一次,重庆市三峡川剧团带着《白露为霜》来到第四届川剧节,借此机会,让我们来聊一聊隆老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塑造过程。
貂蝉、金子和鸣凤
“貂蝉”来自于戏曲作品《貂蝉之死》,是隆学义先生的早期作品。看过这个戏的观众对女主人翁貂蝉的“忠勇”和“刚烈”至今仍记忆犹新。川剧《貂蝉之死》共分为五场:“水淹下邳”“貂蝉休书”“关羽慕蝉”“群雄惊艳”“残月芳魂”。该剧以“三国演义”故事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的情节和人物为创作基础和戏剧文化背景,讲述了善良忠烈的貂蝉爱慕关羽厚德载物又豪放勇猛的英雄气概,却欲嫁之而不得,终而饮剑自尽的悲剧故事。传统折子戏“白门楼”在各地方戏中流布甚广,是一场艺术格调刚健硬朗的“男人戏”,充满了权术的火药味。隆学义独具匠心地将男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和心理角逐,化为了“群雄惊艳”貂蝉美色,而惊起的醋浪情波。曹操及刘、关、张等辈各自处于自己的立场,显示出了对“美女”微妙的反应。貂蝉就仿佛一面镜子,照射出男权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相互攻伐的激烈对抗性特征与“一团和气”障掩下的虚伪性。男性世界的“对抗与虚伪”和女性世界的“忠义、贞烈、纯洁”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貂蝉以纯洁的女性之思渴慕、向往着英雄,而英雄是男权社会的产物,美人在惊艳群雄之后,至多不过作为物品——正如剧作者设计的象征性符号:貂蝉手中的白玉连环,小小扇儿一样,作为群雄逐鹿的筹码被赠送。从貂蝉的角度来说,她修书给关羽以救下邳百姓的计策,足可见她的胆识和爱心,但男权社会并没有看到一个女子的剑胆琴心,她最终还是一个玩物。即使作为玩物,能嫁给大将军关羽,也是善终,但是刘玄德携张飞洞房赠礼,暗示“扶汉兴刘”的戏剧故事情节,把貂蝉最后的幸福希望全部带走了。既然羞了脸儿,罢了扇儿,嫁不得自己的心爱,受了屈辱的貂蝉选择了一个惨烈的死法,表达炽烈的情爱和执拗的忠诚。戏曲艺术形象的极端化处理,让这个人物熠熠生辉。
川剧《金子》始改编创作于1995年,由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担纲主演。初演时保存了曹禺原话剧剧名《原野》。这个从东北文化移植而来的故事,一开始便患上了川剧的不适应症。曹禺笔下的花金子,是一个参杂着野性和性欲的女人,这样的人物形象,川剧的旦角在她的面前显得过于“柔软”,因此川剧《原野》的第一次呈现对曹禺原著的表达就不准确。而创造一个“俏媳妇”金子形象,让川剧演“金子”的贴合度更高。这出川剧的名字因此由《原野》变为了《金子》。隆学义先生比理解一个东北少妇更加熟悉巴蜀媳妇儿,因此他笔下的金子具有巴蜀女人的特点“娇”“俏”“真”“直”“善”,在确立了人物的地方文化性格之后,隆学义着手改编情节桥段。而事实上,他发现传统川剧已经为她准备了大量的身法和程式,去帮助他呈现一个“娇”“俏”的富有地域风情的女人,这也正应了“艺术源于生活”一语。而隐藏在传统川剧旦角“俏丽”之下的,是一个个悲哀的灵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哪一个不是深居闺阁,备受束缚的女性形象,而川剧赋予了她们内敛、隐忍、幽怨的品格,即或是刚烈,也是在隐忍、凄丽的外套下表现,比如说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按照川剧表演的规律,一个美的金子,应该首先是丈夫的妻子,婆婆的媳妇,族弟的嫂嫂……她在表现她的独特个性之前,首先应该表现得温婉、隐忍、善良、规矩。她不能与自然天性对话,而只能与家庭关系对话;她不能讲欲望,而只能讲纯洁的感情——这是一个被传统戏曲样式所设计的,被伦理“极端束缚”的金子形象。此外,金子在舞台上又必须是美的,不能是野蛮的,应该是程式的,节制的,而不应该是轻狂的。善良风情的金子被卷入复仇的风潮之后,会有一个必然结果,那就是选择善良到底。女性本是世间真、善、美的代表,金子在作为第一主角之后,她的戏剧动机只会有一个:阻止虎子的复仇行为——她想跟虎子远走,去到黄金铺路的地方,了却仇虎心头的夺妻之恨;她想留住大星、焦母还有小黑子的性命,因为“冤冤相报何时了?”可是仇虎一心陷入复仇深渊而无法自拔。到这里,川剧《金子》的主题已经离话剧《原野》有距离了:《原野》讲述的是农民复仇的故事,戏剧主要冲突在仇虎与焦阎王寡妻焦母之间直接展开;而《金子》的矛盾中心在于“金子想要阻止仇虎复仇而不能”。阻止复仇,即倡导着以宽容去化解仇恨。宽容——这便是《金子》创新的戏剧主题。川剧《金子》声名远播,其原因并不是因为隆学义先生重复了曹禺,而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颇具巴蜀地域文化色彩的“金子”,并因为“金子”人物形象的成功,带动了整个剧作主题的升华。川剧《金子》中的“金子”形象,体现了“直率”“泼辣”“勇敢”的性格,而在表达过程中,由戏剧主题的深挖而带动的戏剧人物性格深度探索,让观众们懂得,“真诚”“善良”和“宽容”才是金子性格的真正内核。
川剧《鸣凤》改编自四川籍作家巴金小说《家》。这出戏由重庆市三峡川剧团演出,谭继琼因此剧摘取了第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这出戏主要讲述鸣凤追求自由爱情而不得,被封建主义毁灭的故事。鸣凤在巴金的《家》中只是一个“戏份”极少的小人物,她的生命如同萤火虫的光亮倏忽闪烁,最终消弭在阴沉的黑暗中。隆学义的川剧《鸣凤》拮取了萤火虫的意象,奠定了这出戏的唯美基调,并将此意象由歌、舞、说白等戏曲形式加以表现。创作立意点的奇特,使这出戏并不将“铺叙故事”作为叙事重点,而将笔力用于人物情感变化与跌宕的关节点上,该剧分为五场:“情绽”“爱鸣”“惊变”“敲窗”“投湖”。每一场戏的设计,都是为了生动淋漓地呈现一位少女——心灵的成长与挣扎。这种挣扎和成长实际上只基于“纯真”二字。川剧剧本《鸣凤》改编自巴金小说《家》。隆学义在《成都·巴金·<鸣凤>》中写道:“在《家》里,我对丫头鸣凤印象犹深。一朵荷花出水、一枝百合初开也似的少女,她的纯真被暴风撕碎,她的美好为淫雨毁灭。”(注:隆学义:《文心雕虫》,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第338页)如果说《牡丹亭》的杜丽娘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杜丽娘为爱可以超越生死,而遭受封建压迫的鸣凤,则只能投湖以谢真情。
陈白露背后的艰难创造
《白露为霜》改编自曹禺的另一部话剧作品《日出》。如陈白露一般的都市女性,无论是在故事发生的民国时期还是作者生活的当下,在都市环境中俯首皆是。而为了让巴蜀“陈白露”更具有地域特色,隆学义在剧中加入了巴蜀市井的民间环境,例如用四川清音《小放风筝》来表现少女时代的陈白露。陈白露善良,风情,又勇敢果断,有一场戏甚至写到她为救继女“小东西”出火坑,女扮男装深入狼穴,与男人争斗。而从本剧的主旨来看,隆学义对曹禺的“女性主题”进行了生发——更加深入地讨论了女人在现代社会的出路问题。陈白露身上被打上了当下都市女性的性格痕迹和命运困惑: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人皆渴慕幸福,而支撑幸福的到底应该是“物质”,还是“精神”和“自由的理想”?陈白露的精神世界正挣扎在这两种抉择之中:她走向社会,没能经受金钱和物质的诱惑,因此她又有沉沦的一面;而另一面,她心中仍然保持着对当年纯真情爱的眷恋,同时也在向金八这样的恶势力做斗争。隆学义发挥了戏曲写意的优越性,将曹禺《日出》中所蕴藏的象征主义意味进行了深刻开掘。“白露结清霜”的清曲反复吟诵,昭示着该剧的精神内涵:太阳出来了,霜就该化掉了——光明终将属于未来的人们,而丑恶和衰败的东西只能埋藏在过去。”陈白露从少女的清纯、善良发展到进入社会后的泼辣、沉沦,再到最后的觉醒和勇敢挣扎——抒写了一部女性性格成长史。隆学义正视了人类性格的复杂性,也同时抓住了重点,那就是巴蜀女性那份执着的探索意志和坚定的抗争精神。隆学义用戏剧的手法,为陈白露打上了地域文化的标签。
事实上,用戏曲的形式塑造陈白露的形象,是颇有难度的。在写作《金子》和《鸣凤》的时候,隆学义先生都采用了“一人一事”的戏曲叙事法,在立主脑,去枝蔓之后,全剧的人物关系和矛盾都围绕着主角金子和鸣凤旋转起来。而为了写活陈白露,编剧的叙事问题变得更加艰难起来。
2014年,著名文艺评论家马也先生两次在川剧《白露为霜》的研讨会上谈到:“将《日出》改编为戏曲几乎是不可能的。”(注:《隆学义戏剧艺术评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第158页。)话剧《雷雨》是写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悲剧,话剧《日出》则是在写一群人,写社会群体的悲剧式“狂欢”。
“因为要把实际生活中各有因果联系的人生悲剧集中在有限的舞台人物上,就必须使他们互为因果,构成彼此紧密联系的复杂网络。《雷雨》结构的高超处就在于此。但是,当《日出》的题材激动着曹禺的心的时候,《雷雨》的技巧马上使他感到不足甚至厌恶了。在这时,他仍然关心的是人,但却不仅仅是各个人物的命运,而是由这一个个人物构成的一种社会状态,一个完整的社会。要把一种社会状态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展现出来,也需要压缩和集中却不能让读者和观众明确地感觉出来。《日出》着眼的是社会世态的展现,因而它需要的不是每个人生命运的纵向发展过程,而主要是社会世态的展现。”(注:王富仁:《<日出>的结构和人物》,《曹禺研究1979-2009》,吉林文史出版社,第295页。)
话剧《日出》展示了十分广阔的社会画卷,人物复杂而众多,都围绕着“损不足以奉有余”一句话展开。虽然这个戏也称得上“形散而神聚”,而要把它改编成单纯的戏曲故事,还是颇有难度。隆学义先生面对的最直接问题就是,怎样用“一人一事”的口袋装下《日出》这个庞大的文学世界。这个戏为重庆市三峡川剧团的谭继琼而写,“陈白露”就是那个“一人”。而“一事”则难于解决了,本文作者暂且把这个话剧陈白露的故事描绘为:“纯洁的陈白露,本来有着健康的生活和爱情观念,而命运却让她进入尘世,在腐朽混乱的都市市井生活中堕落,渴求光明而不得。她难以抗拒绝望的折磨,终如白露为霜一般,融化在日出之后。”隆学义先生使用了传统文学中的诗话意象,来提纯曹禺原作错综的社会场景和人物故事,像川剧《金子》和《鸣凤》一样,希望让戏剧矛盾围绕主角而旋转。当矛盾繁多而难以贯穿时,他便创造性地以一首小诗贯穿全剧:“芦苇花飞白,白露结清霜。清霜如女郎,女郎绿水旁。日出清霜化,清心泥土藏。”说到底,话剧《日出》结构的松散,使得川剧《白露为霜》难于找到戏剧结构上的发力点。从曹禺提炼的“损不足以奉有余”,到隆学义提纯的“白露结清霜”,两个“日出”故事,都比具有完整情节和冲突的话剧《原野》、《雷雨》或川剧《金子》,具有更加浓重的诗话和象征意味,这是剧作家们在制造戏剧文学创作上的逻辑发力点。站在坚实的戏剧结构上,执着于光明的陈白露才得以立住!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