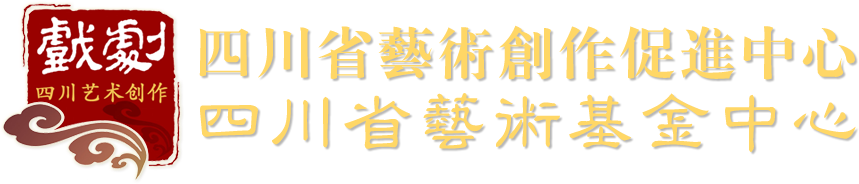
宝桢精神历久弥新 川腔川韵常演常新
——观新编川剧《丁宝桢》有感
黄月
四川省第三届川剧汇演如火如荼进行之时,笔者有幸于9月16日晚于四川大剧院二度观演川剧《丁宝桢》。该剧由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创排演出,自首演以来,已巡演多场,今日演出相较以往有改动更有提升,可谓不变初心、常演常新。丁宝桢一角由“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王超与二级演员、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王耀超分饰扮演;丁宝桢夫人由“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王玉梅倾情演绎;剧院诸多优秀中青年演员参与演出。纵观全剧由守卫桢楠、宫保赴宴、清风蔚然、大修堤堰、激流勇进、无价宝桢六场戏为观众勾勒出一位勤政爱民、大公无私的无价宝桢形象。

一、承川剧“高腔”之大气磅韵味,开篇即以风骨立人
“为官如斯,护佑苍生”,短短八字,恰似高腔起调般掷地有声,瞬间锚定丁宝桢入川后的初心底色。彼时的四川,百姓在“风吹叶响珠泪弹”的苦难里挣扎,“官府靠不住”的喟叹早已成了民间共识——毕竟过往官吏多是“一个模子老套路”,高高在上的姿态,让民生疾苦成了无人问津的泡影。直到丁宝桢的到来,这片被苦难笼罩的土地,才迎来了不一样的曙光。
从“少爷的马要踩死人了”的鸣锣开道划破街巷,百姓一度以为“光打雷不下雨,光说不做”的新官来了,到丁宝桢躬身寻访时发自肺腑的一句“高高在上听告禀,从来官高眼于顶,如今跪看百姓才分明”,伴着川剧高腔特有的磅礴气势,瞬间撞进人心;紧接着,帮腔悠悠响起:“桢楠树,千岁龄,今日初见官拜民”,高亢激越的高腔,结合川剧独树一帜的帮腔与紧凑锣鼓相融,生动再现丁宝桢力阻盗伐、护木安民的果敢气魄与傲人风骨。唱词紧扣川音语调,字字入腔,既显文采又不失通俗,使人物形象立体可感。可见开篇“守卫桢楠”便稳稳奠定全篇基调,守卫的何止桢楠,更是千百年来百姓心中的那份信仰,是能俯下身来,切身体会百姓疾苦的宝桢对百姓的那份护佑,也是让百姓看到了 “官府靠得住” 的希望。
二、借川剧 “四功五法”,塑人物与场景,融合“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叙事与情感丁宝桢“布衣巡查”与“跪看百姓”,常贵“骄横”与“戴枷”,“万民修堰”与“丁小五救常贵”,演员的唱念做打、翻滚扑跌贯穿其中,以川剧传统表现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增强演员表现力,使人物形象丰富且饱满,是川剧表演注重“手眼身法步”的深刻体现,运用川剧程式化动作通过细腻身段等展现人物性格、还原关键场景,也让演出更具视觉张力。
结合丁宝桢宴请百官时,臭馊稻米赴宴,怒斥贪腐;贿赂款变赈灾银为修都江堰筹措银两;将各地泥土封箱典当一万两赈灾银的情节设置;包括修堤堰时大胆以铁链锁石笼换陈旧竹笼,都显示其过人胆识,这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叙事与情感,避免空洞无味的乏陈说教,让人看得过瘾的同时不觉已然完成一次灵魂的涤荡洗礼。

三、循川剧“以小见大”传统表现手法出新意,一物多用喻多景,虚实相生交相呼应
川剧舞台布景擅长“一桌二椅”“一椅多用”的表现手法,借简单道具象征复杂场景,通过不同的摆放位置来使场景千变万化,这样在表演中“以一当十”的表现手法强化了桌椅的象征意义,使其成为剧情的有机组成部分,完美贴合川剧虚实相生的舞台风格。
丁宝桢携“宫保鸡丁”归家,简单的“一桌二椅”搭配极简屏风设计,“柴廊小径翠竹轩”便是一位官居一品大员的总督之家,这何尝不是丁宝桢清廉为官治家的真实写照。万民大修堤堰时,表现“洪水汹涌袭来”时,表现“安澜桥”时,表现“都江堰堤坝”时,在特定的舞台氛围下,椅子的不同摆设与运用,在新编川剧中也是极富表现力的,这又何尝不是川剧舞台的灵活设置辅以演员充分表现力的佐证。
用川剧大靠武生的形象——由演员扮演的“桢楠树”屹立台中,受百姓虔诚跪拜,何尝不是象征着丁宝桢受百姓爱戴的精神品格,恰似把丁宝桢的内心情感和人物品格做了意象化的表达,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极具舞台表现力和感染力。
新编川剧《丁宝桢》没有将先贤故事束之高阁,而是以川剧“高腔”的磅礴、“四功五法”的鲜活、“以小见大”的巧思,让丁宝桢的勤政爱民、刚正不阿,化作台下观众可感、可叹、可敬的精神力量——这既是对川剧传统的守正,也是对时代审美的创新。丁宝桢“护佑苍生”的初心,穿越百年仍能叩击现代人的心灵;而川剧这门古老艺术,也因这样的新编剧目,在传承中不断生长。当“桢楠树”的意象仍在脑海中矗立,我们便知:好的故事从不会过时,好的艺术总能常演常新,而像丁宝桢这样的精神丰碑,更会在岁月流转中,始终照亮人心。
文章经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图片源自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宝桢精神历久弥新 川腔川韵常演常新
——观新编川剧《丁宝桢》有感
黄月
四川省第三届川剧汇演如火如荼进行之时,笔者有幸于9月16日晚于四川大剧院二度观演川剧《丁宝桢》。该剧由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创排演出,自首演以来,已巡演多场,今日演出相较以往有改动更有提升,可谓不变初心、常演常新。丁宝桢一角由“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王超与二级演员、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王耀超分饰扮演;丁宝桢夫人由“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王玉梅倾情演绎;剧院诸多优秀中青年演员参与演出。纵观全剧由守卫桢楠、宫保赴宴、清风蔚然、大修堤堰、激流勇进、无价宝桢六场戏为观众勾勒出一位勤政爱民、大公无私的无价宝桢形象。

一、承川剧“高腔”之大气磅韵味,开篇即以风骨立人
“为官如斯,护佑苍生”,短短八字,恰似高腔起调般掷地有声,瞬间锚定丁宝桢入川后的初心底色。彼时的四川,百姓在“风吹叶响珠泪弹”的苦难里挣扎,“官府靠不住”的喟叹早已成了民间共识——毕竟过往官吏多是“一个模子老套路”,高高在上的姿态,让民生疾苦成了无人问津的泡影。直到丁宝桢的到来,这片被苦难笼罩的土地,才迎来了不一样的曙光。
从“少爷的马要踩死人了”的鸣锣开道划破街巷,百姓一度以为“光打雷不下雨,光说不做”的新官来了,到丁宝桢躬身寻访时发自肺腑的一句“高高在上听告禀,从来官高眼于顶,如今跪看百姓才分明”,伴着川剧高腔特有的磅礴气势,瞬间撞进人心;紧接着,帮腔悠悠响起:“桢楠树,千岁龄,今日初见官拜民”,高亢激越的高腔,结合川剧独树一帜的帮腔与紧凑锣鼓相融,生动再现丁宝桢力阻盗伐、护木安民的果敢气魄与傲人风骨。唱词紧扣川音语调,字字入腔,既显文采又不失通俗,使人物形象立体可感。可见开篇“守卫桢楠”便稳稳奠定全篇基调,守卫的何止桢楠,更是千百年来百姓心中的那份信仰,是能俯下身来,切身体会百姓疾苦的宝桢对百姓的那份护佑,也是让百姓看到了 “官府靠得住” 的希望。
二、借川剧 “四功五法”,塑人物与场景,融合“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叙事与情感丁宝桢“布衣巡查”与“跪看百姓”,常贵“骄横”与“戴枷”,“万民修堰”与“丁小五救常贵”,演员的唱念做打、翻滚扑跌贯穿其中,以川剧传统表现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增强演员表现力,使人物形象丰富且饱满,是川剧表演注重“手眼身法步”的深刻体现,运用川剧程式化动作通过细腻身段等展现人物性格、还原关键场景,也让演出更具视觉张力。
结合丁宝桢宴请百官时,臭馊稻米赴宴,怒斥贪腐;贿赂款变赈灾银为修都江堰筹措银两;将各地泥土封箱典当一万两赈灾银的情节设置;包括修堤堰时大胆以铁链锁石笼换陈旧竹笼,都显示其过人胆识,这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叙事与情感,避免空洞无味的乏陈说教,让人看得过瘾的同时不觉已然完成一次灵魂的涤荡洗礼。

三、循川剧“以小见大”传统表现手法出新意,一物多用喻多景,虚实相生交相呼应
川剧舞台布景擅长“一桌二椅”“一椅多用”的表现手法,借简单道具象征复杂场景,通过不同的摆放位置来使场景千变万化,这样在表演中“以一当十”的表现手法强化了桌椅的象征意义,使其成为剧情的有机组成部分,完美贴合川剧虚实相生的舞台风格。
丁宝桢携“宫保鸡丁”归家,简单的“一桌二椅”搭配极简屏风设计,“柴廊小径翠竹轩”便是一位官居一品大员的总督之家,这何尝不是丁宝桢清廉为官治家的真实写照。万民大修堤堰时,表现“洪水汹涌袭来”时,表现“安澜桥”时,表现“都江堰堤坝”时,在特定的舞台氛围下,椅子的不同摆设与运用,在新编川剧中也是极富表现力的,这又何尝不是川剧舞台的灵活设置辅以演员充分表现力的佐证。
用川剧大靠武生的形象——由演员扮演的“桢楠树”屹立台中,受百姓虔诚跪拜,何尝不是象征着丁宝桢受百姓爱戴的精神品格,恰似把丁宝桢的内心情感和人物品格做了意象化的表达,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极具舞台表现力和感染力。
新编川剧《丁宝桢》没有将先贤故事束之高阁,而是以川剧“高腔”的磅礴、“四功五法”的鲜活、“以小见大”的巧思,让丁宝桢的勤政爱民、刚正不阿,化作台下观众可感、可叹、可敬的精神力量——这既是对川剧传统的守正,也是对时代审美的创新。丁宝桢“护佑苍生”的初心,穿越百年仍能叩击现代人的心灵;而川剧这门古老艺术,也因这样的新编剧目,在传承中不断生长。当“桢楠树”的意象仍在脑海中矗立,我们便知:好的故事从不会过时,好的艺术总能常演常新,而像丁宝桢这样的精神丰碑,更会在岁月流转中,始终照亮人心。
文章经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图片源自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