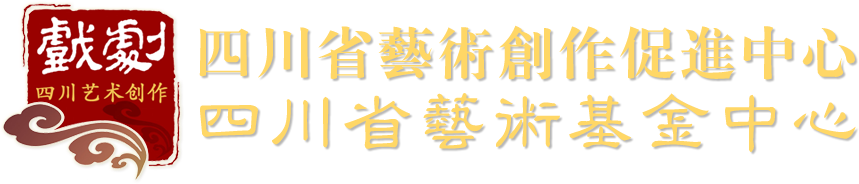
琴韵山水的艺术思考——《山止川行——吴玥钢琴音乐会》的多元解读
陈斌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仲夏蓉城,琴声流觞;山水形胜,乐启华章。
2025年7月20日,《山止川行——吴玥钢琴音乐会》在城市音乐厅室内音乐厅如期而至。高山的肃穆庄重,流水的博大广阔;历史的沉重深邃,现代的节奏跃动;西方音乐中的悠悠琴声,东方艺术里的层层戏韵;千秋文脉的传承,时代风潮的脉动,在这场别有格致的音乐会中汇聚、对话,勾勒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在传统与现代对话中的艺术思考。
上篇《山止》:峰峦叠嶂的历史镜像
音乐会以“山止川行”为主题,开篇即以序曲《山》定格音乐会。这是一首委约作品,由作曲家熬翔担纲创作。作品如山肃穆庄重,又兼具万山磅礴的气象。这首作品对音乐会上篇的安排和呈现具有重要的揭示作用。
寥寥数笔,妙色生香;簇簇音韵,开宗明义。
序曲之后,步入正题。先是一首巴洛克时期亨德尔的作品《G大调恰空》。这首作品是一块试金石,是理解巴洛克变奏艺术的一把钥匙和一扇大门,其技术挑战与深刻表现力并存,许多国际大赛参赛选手选此作品参赛,难度可见一斑。这首作品是巴洛克羽管键琴文献中最经典的固定低音变奏曲之一,从庄严的低音主题起步,逐渐发展为炫技性的快速音群;从简单的复调对位到中期的三声部赋格交织,再到后期变奏的华丽技巧,直至尾声双手齐奏的雷霆万钧,整首作品需要强有力的技巧控制、结构把控、音乐处理能力。在这场左手的耐力赛中,演奏者以理性的控制、女性特有的细腻音乐处理、对细致变化的敏感把握完成了音乐诠释。羽管键琴般的音色、歌唱般的旋律、戏剧性的张力、严密的逻辑演进,带领我们进入了巴洛克的时空之中。
从巴洛克的山峰上走下来,我们随着演奏者的脚步进入了古典主义,贝多芬《第七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悄然而至。这是贝多芬早期的作品,是其早期钢琴奏鸣曲中的杰作,兼具古典主义的严谨与对浪漫主义精神的探索。第一乐章要求演奏者平衡动力推进与古典优雅。演奏者以不凡的驾驭能力呈现出快速流动的音群、和弦的欢呼跳跃、华彩段落的欢腾,体现出了古典主义的人文精神。
越过古典时期的峰峦,转身而过便来到了浪漫主义时期,呈现在听众面前的便是勃拉姆斯的三首钢琴小品。这三首独立的小品,每一首都具有独特的性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时而激情时而忧郁,充满勃拉姆斯式的厚重;时而婉转如歌,旋律优美,带着摇篮曲般的抚慰;时而坚定有力,充满着戏剧张力;时而深沉悲怆,如泣如诉。色彩的多样变换,情绪的多愁善感,心绪的多维蝶变,情感的多重细腻,哲学般的思考与浪漫的情思相互交织,让钢琴小品“横看成岭侧成峰”,很考演奏者的功底。
从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历史纵深中走出来之后,演奏者选择了当代作曲家卡尔·维恩的五首钢琴小品。作为澳大利亚当代最重要的作曲家,卡尔·维恩的钢琴小品以凝练的结构、鲜明的节奏、冷峻中暗涌的诗意而著称。他的这些作品在技术挑战与艺术深度间获得了巧妙的平衡。左手低音的脉冲、右手漂浮的云彩,冰晶般的泛音、孤寂的旋律、机械般的大锤、瞬间的爆发、钟表齿轮般的逻辑变化,像澳洲荒原上从天边刮过来的一阵阵风,野性与理性交织,荒诞与诗性隐喻,工业节奏与人文哲思对话,彰显着“澳洲荒漠的生命力隐藏法则”。演奏者要在这独特的隐喻中寻找现代人的心灵彼岸,要在逼迫乐器揭示灵魂深处的锈迹与光芒中寻找出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对演奏者还是听众,都是一场丛林冒险。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指出,“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这场音乐会的上篇带给我们的便是“层层叠叠的山”,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钢琴世界里不同的“山”的丰富层次。巴洛克的光芒,古典主义的理性,浪漫主义的激情,当代精神的隐喻,或近或远,或明或暗,高远之色的崇安感,深远之色的神秘感,平远之色的空灵感一一呈现,让人感受到了钢琴音乐的历史纵深感。庄重肃穆,林木苍翠。
“山止”之处,是静穆的伟大;琴声流淌,是心灵的映照。
演奏家在上篇以“山行者”的态度,带领我们走进了钢琴的世界,走进了作曲家的心灵,走进了历史的纵深处。
琴声结束,回首来时路,身后已是峰峦叠嶂,气象万千。

下篇《川行》:海纳百川的时代欢歌
山止川行,水行千里。
从高山仰止般的历史纵深处走出来之后,音乐会便进入了浩浩的川行之旅。作为引子,委约创作的钢琴曲《行水》从山谷中汩汩而出,开启了新的篇章,呈现出“上善若水”的境界。
引子《行水》之后,便是琵琶协奏曲《云想·花想》了。音乐会的格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琵琶与钢琴展开了思想的对话、情感的共鸣,优美的旋律充满着女性的柔美与相思,灵动的节奏跳动着心灵的音符,如泣如诉鸟惊心,起伏跌宕花溅泪,情感的波涛在山川中百折千回,灿烂的人生与永恒的爱情纠缠。琵琶珠落玉盘,钢琴月映寒江,琵琶与钢琴之间配合默契,架设了爱情的鹊桥,倾诉着动人的心扉,如云中燕、似花中蝶,表达了“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的倾心倾情。
在一段中西乐器的共鸣之后,音乐会便进入了更为大胆的探索阶段。川剧弹戏《上关拜寿》、川剧高腔《绣襦记》选段登场,与钢琴之间展开了别开生面的合作。用钢琴为传统川剧伴奏,这本身就极具挑战性,为传统戏曲的现代传播探索了新的路径。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戏曲还是那个戏曲,钢琴伴奏的编配、钢琴的伴奏却是全新的,是青年艺术工作者们勇于突破传统、守正创新的一次突破,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更需要胆识和才情。两名青年川剧演员登场演唱,钢琴伴奏紧密配合,共同完成了这一勇敢的尝试,受到了观众的肯定。
悠悠戏韵后,童声合唱的《星星河》像满天星辰在水面闪耀着粼粼波光。这是一首关于梦想、成长、勇气的乐曲。“云伴山,山伴我,山的那边有什么,爷爷说有条星星河,装着数不清的梦淌满亮晶晶的河”,山里的风刮过了山岗,山里的梦跃上了星河。清澈透明的童声、晶莹剔透的琴音,飞翔的梦想映照出时代的欢乐。
山止川行,星语成河。海纳百川,岁月如歌。《星星河》唱出了童年的心声,《山止川行》为音乐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从引子《山止》到《川行》再到《山止川行》,这一条主线纵向串联出历史的纵深感,横向串联出中西文明对话的交织感,让这一场音乐会具有了相当的思想深度、人文丰度、情感温度。
诚然,这不是一场炫技性质的音乐会,也不是一场先锋现代的音乐会。但是,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再到现当代,从钢琴的主题叙事到与琵琶、传统戏曲、合唱的融合,既有忠于严肃音乐的礼敬,又有打破陈规的创新探索,多角度的艺术思考、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多样态的音乐色彩、多维度的情感表达,让这场音乐会既保持了山止的崇高感,又具备了川行的优美感;既有高山仰止般的厚度与凝重,又具有水利万物的包容与不争,对青年艺术家来说是一种不小的挑战,也展现出了当代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深入思考与责任担当。
这场音乐会以山水为意象,以琴键为媒介,既丈量了西方音乐的历史纵深,又探索了中西和鸣的当代可能。当琴键与戏曲共鸣,与童声共吟,与山川共情,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艺的融合,更是文化自信的生动诠释。青年艺术家以“山止川行”的美学姿态,完成了从技艺展示到文化表达的升华,彰显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文章经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图片源自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琴韵山水的艺术思考——《山止川行——吴玥钢琴音乐会》的多元解读
陈斌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仲夏蓉城,琴声流觞;山水形胜,乐启华章。
2025年7月20日,《山止川行——吴玥钢琴音乐会》在城市音乐厅室内音乐厅如期而至。高山的肃穆庄重,流水的博大广阔;历史的沉重深邃,现代的节奏跃动;西方音乐中的悠悠琴声,东方艺术里的层层戏韵;千秋文脉的传承,时代风潮的脉动,在这场别有格致的音乐会中汇聚、对话,勾勒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在传统与现代对话中的艺术思考。
上篇《山止》:峰峦叠嶂的历史镜像
音乐会以“山止川行”为主题,开篇即以序曲《山》定格音乐会。这是一首委约作品,由作曲家熬翔担纲创作。作品如山肃穆庄重,又兼具万山磅礴的气象。这首作品对音乐会上篇的安排和呈现具有重要的揭示作用。
寥寥数笔,妙色生香;簇簇音韵,开宗明义。
序曲之后,步入正题。先是一首巴洛克时期亨德尔的作品《G大调恰空》。这首作品是一块试金石,是理解巴洛克变奏艺术的一把钥匙和一扇大门,其技术挑战与深刻表现力并存,许多国际大赛参赛选手选此作品参赛,难度可见一斑。这首作品是巴洛克羽管键琴文献中最经典的固定低音变奏曲之一,从庄严的低音主题起步,逐渐发展为炫技性的快速音群;从简单的复调对位到中期的三声部赋格交织,再到后期变奏的华丽技巧,直至尾声双手齐奏的雷霆万钧,整首作品需要强有力的技巧控制、结构把控、音乐处理能力。在这场左手的耐力赛中,演奏者以理性的控制、女性特有的细腻音乐处理、对细致变化的敏感把握完成了音乐诠释。羽管键琴般的音色、歌唱般的旋律、戏剧性的张力、严密的逻辑演进,带领我们进入了巴洛克的时空之中。
从巴洛克的山峰上走下来,我们随着演奏者的脚步进入了古典主义,贝多芬《第七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悄然而至。这是贝多芬早期的作品,是其早期钢琴奏鸣曲中的杰作,兼具古典主义的严谨与对浪漫主义精神的探索。第一乐章要求演奏者平衡动力推进与古典优雅。演奏者以不凡的驾驭能力呈现出快速流动的音群、和弦的欢呼跳跃、华彩段落的欢腾,体现出了古典主义的人文精神。
越过古典时期的峰峦,转身而过便来到了浪漫主义时期,呈现在听众面前的便是勃拉姆斯的三首钢琴小品。这三首独立的小品,每一首都具有独特的性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时而激情时而忧郁,充满勃拉姆斯式的厚重;时而婉转如歌,旋律优美,带着摇篮曲般的抚慰;时而坚定有力,充满着戏剧张力;时而深沉悲怆,如泣如诉。色彩的多样变换,情绪的多愁善感,心绪的多维蝶变,情感的多重细腻,哲学般的思考与浪漫的情思相互交织,让钢琴小品“横看成岭侧成峰”,很考演奏者的功底。
从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历史纵深中走出来之后,演奏者选择了当代作曲家卡尔·维恩的五首钢琴小品。作为澳大利亚当代最重要的作曲家,卡尔·维恩的钢琴小品以凝练的结构、鲜明的节奏、冷峻中暗涌的诗意而著称。他的这些作品在技术挑战与艺术深度间获得了巧妙的平衡。左手低音的脉冲、右手漂浮的云彩,冰晶般的泛音、孤寂的旋律、机械般的大锤、瞬间的爆发、钟表齿轮般的逻辑变化,像澳洲荒原上从天边刮过来的一阵阵风,野性与理性交织,荒诞与诗性隐喻,工业节奏与人文哲思对话,彰显着“澳洲荒漠的生命力隐藏法则”。演奏者要在这独特的隐喻中寻找现代人的心灵彼岸,要在逼迫乐器揭示灵魂深处的锈迹与光芒中寻找出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对演奏者还是听众,都是一场丛林冒险。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指出,“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这场音乐会的上篇带给我们的便是“层层叠叠的山”,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钢琴世界里不同的“山”的丰富层次。巴洛克的光芒,古典主义的理性,浪漫主义的激情,当代精神的隐喻,或近或远,或明或暗,高远之色的崇安感,深远之色的神秘感,平远之色的空灵感一一呈现,让人感受到了钢琴音乐的历史纵深感。庄重肃穆,林木苍翠。
“山止”之处,是静穆的伟大;琴声流淌,是心灵的映照。
演奏家在上篇以“山行者”的态度,带领我们走进了钢琴的世界,走进了作曲家的心灵,走进了历史的纵深处。
琴声结束,回首来时路,身后已是峰峦叠嶂,气象万千。

下篇《川行》:海纳百川的时代欢歌
山止川行,水行千里。
从高山仰止般的历史纵深处走出来之后,音乐会便进入了浩浩的川行之旅。作为引子,委约创作的钢琴曲《行水》从山谷中汩汩而出,开启了新的篇章,呈现出“上善若水”的境界。
引子《行水》之后,便是琵琶协奏曲《云想·花想》了。音乐会的格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琵琶与钢琴展开了思想的对话、情感的共鸣,优美的旋律充满着女性的柔美与相思,灵动的节奏跳动着心灵的音符,如泣如诉鸟惊心,起伏跌宕花溅泪,情感的波涛在山川中百折千回,灿烂的人生与永恒的爱情纠缠。琵琶珠落玉盘,钢琴月映寒江,琵琶与钢琴之间配合默契,架设了爱情的鹊桥,倾诉着动人的心扉,如云中燕、似花中蝶,表达了“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的倾心倾情。
在一段中西乐器的共鸣之后,音乐会便进入了更为大胆的探索阶段。川剧弹戏《上关拜寿》、川剧高腔《绣襦记》选段登场,与钢琴之间展开了别开生面的合作。用钢琴为传统川剧伴奏,这本身就极具挑战性,为传统戏曲的现代传播探索了新的路径。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戏曲还是那个戏曲,钢琴伴奏的编配、钢琴的伴奏却是全新的,是青年艺术工作者们勇于突破传统、守正创新的一次突破,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更需要胆识和才情。两名青年川剧演员登场演唱,钢琴伴奏紧密配合,共同完成了这一勇敢的尝试,受到了观众的肯定。
悠悠戏韵后,童声合唱的《星星河》像满天星辰在水面闪耀着粼粼波光。这是一首关于梦想、成长、勇气的乐曲。“云伴山,山伴我,山的那边有什么,爷爷说有条星星河,装着数不清的梦淌满亮晶晶的河”,山里的风刮过了山岗,山里的梦跃上了星河。清澈透明的童声、晶莹剔透的琴音,飞翔的梦想映照出时代的欢乐。
山止川行,星语成河。海纳百川,岁月如歌。《星星河》唱出了童年的心声,《山止川行》为音乐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从引子《山止》到《川行》再到《山止川行》,这一条主线纵向串联出历史的纵深感,横向串联出中西文明对话的交织感,让这一场音乐会具有了相当的思想深度、人文丰度、情感温度。
诚然,这不是一场炫技性质的音乐会,也不是一场先锋现代的音乐会。但是,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再到现当代,从钢琴的主题叙事到与琵琶、传统戏曲、合唱的融合,既有忠于严肃音乐的礼敬,又有打破陈规的创新探索,多角度的艺术思考、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多样态的音乐色彩、多维度的情感表达,让这场音乐会既保持了山止的崇高感,又具备了川行的优美感;既有高山仰止般的厚度与凝重,又具有水利万物的包容与不争,对青年艺术家来说是一种不小的挑战,也展现出了当代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深入思考与责任担当。
这场音乐会以山水为意象,以琴键为媒介,既丈量了西方音乐的历史纵深,又探索了中西和鸣的当代可能。当琴键与戏曲共鸣,与童声共吟,与山川共情,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艺的融合,更是文化自信的生动诠释。青年艺术家以“山止川行”的美学姿态,完成了从技艺展示到文化表达的升华,彰显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文章经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图片源自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