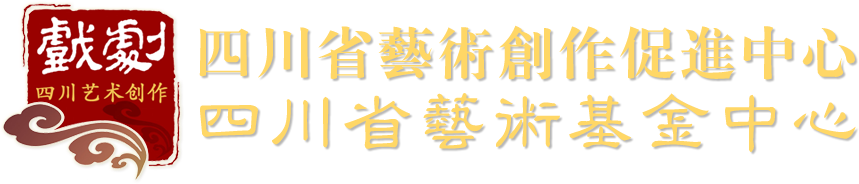
拆字断权柄,声腔见民心
邬丹 四川省美术家协会活动组织部副研究馆员
当遂宁市川剧团的锣鼓声在四川大剧院响起,这部由胡成德改编自关汉卿杂剧的川剧《智斩鲁斋郎》以弹戏的铿锵、高腔的婉转,将北宋朝堂的权与法、智与义搬上舞台。该剧目是遂宁市川剧团参加四川省川剧汇演活动以来第三部包公戏系列的力作。这部作品并非简单的历史故事复刻,而是以川剧特有的程式,剖开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大于法”的深层矛盾,更以“拆字斩奸”的戏剧巧思,完成了对“包公符号”的当代诠释——它既是对古典公案戏精神内核的传承,也是地方戏曲在当代文艺语境下,探索“传统与现实对话”的一次成功实践。

一、“孝治”“铁券丹书”与“拆字计”的三重博弈
剧中鲁斋郎所持的“铁券丹书”,并非虚构的戏剧道具,而是中国封建皇权制度下“法外特权”的象征,背后更深深扎根于北宋“孝治天下”的治国根基。北宋以“孝”为伦理核心与政治纲领,仁宗对“先皇遗命”的敬畏,表面是对先祖意志的遵从,本质上既是对皇权传承合法性的维护,更是“孝治”理念在皇权运作中的直接体现——君主需以“尊祖尽孝”树立统治权威,这份孝的责任与担当,却在鲁斋郎的恶行面前陷入了两难。当法律条文与皇权特权碰撞时,制度漏洞因“孝”的介入更显尖锐:鲁斋郎的恶行并非无法可治,而是借“先皇遗命”披上“孝”的外衣,成为“有权免治”的护身符;包拯的困境也并非无计可施,而是若直接对抗“先皇遗命”,便会陷入“违逆皇权、不敬孝道”的政治漩涡,沦为无权施计的困局。这种困境,不仅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人治与法治的博弈,更是孝治原则下,公平正义与皇权伦理的激烈碰撞。

包拯的“拆字计”,恰恰是在“孝”的约束下对制度困境的戏剧化突破,是对仁宗“孝治”心理的精准回应。将“鲁斋郎”拆改为“鱼齐即”奏请圣裁,再补全笔画定案问斩,这一情节看似是文字游戏,实则蕴含着兼顾孝与义的深刻智慧:它既没有直接否定“先皇遗命”,维护了仁宗“尊祖尽孝”的政治形象(上顺皇意),避免君主陷入“不孝”的舆论争议,又以“技术手段” 绕开特权壁垒,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朴素追求(下得民心)。这一情节不是简单的“智慧炫耀”,而是古典文人对“孝治”语境下“理想政治”的想象性建构——在不触碰“孝”的核心原则、不撼动皇权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个体的智慧与胆识,在“孝”与“义”的缝隙中寻求正义的可能,让“孝治”不再是包庇恶行的借口,而是与公平正义相辅相成的政治伦理。这种建构,与关汉卿原著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却因“孝”的融入更具现实张力与人性温度。

元杂剧中的“包公戏”,本就是对元代社会“权豪势要横行” 的现实批判,关汉卿借包公之口,喊出“王法条条诛滥官” 的呐喊;而今川剧的改编,并未消解这份批判力度,反而以川剧生活化的表演特质,结合历史背景,让这份批判更具共情力——当李四、张珪等平民百姓在舞台上哭诉妻离子散之苦,当老旦演员以“如泣如诉”的唱腔传递绝望,观众既能感受到鲁斋郎借孝之名行特权之恶的荒谬,也能理解仁宗在孝治与民生之间的两难,更能共情包拯在尽孝与为民之间的挣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勾连,让作品超越了戏剧的范畴,不仅批判了封建时代的特权乱象,更引发当代观众对“规则与人情”“传统美德与社会公平”“特权现象”关系的深度思考。
二、从“铁面无私”到“纠结的刚正”,包公形象的人性化突破
在传统戏曲舞台上,包公往往是“神化”的符号:黑面、额间月牙、刚正不阿,仿佛天生没有犹豫与软弱。但川剧《智斩鲁斋郎》却大胆地撕开了这层“符号外衣”,如第五场“探访”与最终的“智铡”篇章中,着重刻画了包拯为难与纠结的情绪——刚正不阿的人也会为难,也会有各种纠结在他的思绪里。这段表演打破了观众对包公的固有认知:他不再是无所不能的正义机器,而是有血有肉的官员,要在皇权压力与百姓期盼之间权衡,要在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之间抉择。

这种“人性化重塑”,是对“包公符号 ”的深度挖掘。剧中包拯那句“贤侄,可否给叔父一个面子”的台词,曾被部分观众质疑“不符合包公形象”,但从学术视角看,这恰恰是作品的点睛之笔:它承认了包拯作为“朝堂官员”的身份局限性——他无法像民间传说中那样“铡刀一开,皇权不问”,只能在人际关系的缝隙中寻求解决之道。这种不完美的正义,比完美的神化更具现实说服力:它告诉观众,正义的实现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爽快,而是步步为营的坚持。
更值得关注的是,剧中女性角色的塑造,为“包公戏”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唱词“包青天也有你的半边天”,看似简单一句,却打破了传统公案戏中“女性仅为受害者”的刻板定位——它暗示着“正义”不仅是对男性权益的维护,也应包含对女性尊严的尊重。李母(彭春燕饰)的唱腔尤为典型:高亢的“亮音”中裹着温润,这种声腔特质,将母亲的坚韧与平民的不屈融为一体,让女性角色不再是推动剧情的工具人,而是承载民心的重要载体。这种改编,呼应了当代社会对性别平等的追求,让古典戏剧有了现代意识。

三、川剧的艺术突围,用川剧讲好中国故事
《智斩鲁斋郎》的成功,在于它守住了川剧的“根”,又扎下了新的“芽”。作品充分发挥了川剧“帮打唱”的声腔优势:净角(刘世虎饰包公)的唱腔浑厚圆润,配合“勾脸”与“功架”,将包公的伟岸形象立得扎实;“帮腔”的穿插则如画外音般,将观众的情绪引入剧情深处——当包公纠结时,帮腔的婉转传递出民心的期盼;当鲁斋郎嚣张时,弹戏的急促又烘托出正义的紧迫感。这种“声腔与情感”的高度融合,正是川剧“以声传情、以腔塑人”的精髓所在。
在叙事结构与舞美设计上,作品又展现了地方剧团的当代视野。全剧“抢亲、情深、巧救、夜抢、探访、请旨、智铡”七场戏,删繁就简,避免了传统戏曲“叙事拖沓”的弊端,以“鲁斋郎作恶—百姓受难—包公施计”的紧凑节奏,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舞美服装华丽精致,并非“经费堆砌”的炫技,而是以简约的布景(如朝堂的威严、民宅的破败)形成视觉对比,强化了权与民的矛盾冲突。这种“传统程式+现代审美”的融合,证明川剧无需迎合潮流而失本,只需找准定位而创新,便能在当代文艺主流行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遂宁市川剧团作为地方院团,虽无国家级院团的资源优势与流量IP加持,却凭借“四梁八柱”的整齐阵容及对川剧花脸声腔艺术的坚守,将古典公案戏《智斩鲁斋郎》演绎得“戏味浓郁、戏韵悠长”,这印证了川剧的生命力不在于复制经典,而在于以地方独特语言解读经典故事的当代价值,用演员扎实功力传递传统文化精神力量——正如剧中李母“亮得明晰,又透着点烟火气的暖”的唱腔,将大历史转化为小叙事,让观众在声腔与表演中感知传统文化与自身生活的紧密关联。当大幕落下、包公身影定格,从关汉卿元杂剧到如今川剧改编,斩鲁斋郎的故事能流传数百年,正因它触及对特权的反抗、对正义的渴望这一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而川剧的演绎更为此注入新的生命力,也让我们确信:传统不是束缚创新的枷锁,而是滋养创新的土壤;地方戏曲亦非小众喜好,而是能与当代观众对话、与现实社会共鸣的“活态文化”,因为它们讲述的不仅是过去的故事,更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正义与民心。
文章经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图片源自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拆字断权柄,声腔见民心
邬丹 四川省美术家协会活动组织部副研究馆员
当遂宁市川剧团的锣鼓声在四川大剧院响起,这部由胡成德改编自关汉卿杂剧的川剧《智斩鲁斋郎》以弹戏的铿锵、高腔的婉转,将北宋朝堂的权与法、智与义搬上舞台。该剧目是遂宁市川剧团参加四川省川剧汇演活动以来第三部包公戏系列的力作。这部作品并非简单的历史故事复刻,而是以川剧特有的程式,剖开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大于法”的深层矛盾,更以“拆字斩奸”的戏剧巧思,完成了对“包公符号”的当代诠释——它既是对古典公案戏精神内核的传承,也是地方戏曲在当代文艺语境下,探索“传统与现实对话”的一次成功实践。

一、“孝治”“铁券丹书”与“拆字计”的三重博弈
剧中鲁斋郎所持的“铁券丹书”,并非虚构的戏剧道具,而是中国封建皇权制度下“法外特权”的象征,背后更深深扎根于北宋“孝治天下”的治国根基。北宋以“孝”为伦理核心与政治纲领,仁宗对“先皇遗命”的敬畏,表面是对先祖意志的遵从,本质上既是对皇权传承合法性的维护,更是“孝治”理念在皇权运作中的直接体现——君主需以“尊祖尽孝”树立统治权威,这份孝的责任与担当,却在鲁斋郎的恶行面前陷入了两难。当法律条文与皇权特权碰撞时,制度漏洞因“孝”的介入更显尖锐:鲁斋郎的恶行并非无法可治,而是借“先皇遗命”披上“孝”的外衣,成为“有权免治”的护身符;包拯的困境也并非无计可施,而是若直接对抗“先皇遗命”,便会陷入“违逆皇权、不敬孝道”的政治漩涡,沦为无权施计的困局。这种困境,不仅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人治与法治的博弈,更是孝治原则下,公平正义与皇权伦理的激烈碰撞。

包拯的“拆字计”,恰恰是在“孝”的约束下对制度困境的戏剧化突破,是对仁宗“孝治”心理的精准回应。将“鲁斋郎”拆改为“鱼齐即”奏请圣裁,再补全笔画定案问斩,这一情节看似是文字游戏,实则蕴含着兼顾孝与义的深刻智慧:它既没有直接否定“先皇遗命”,维护了仁宗“尊祖尽孝”的政治形象(上顺皇意),避免君主陷入“不孝”的舆论争议,又以“技术手段” 绕开特权壁垒,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朴素追求(下得民心)。这一情节不是简单的“智慧炫耀”,而是古典文人对“孝治”语境下“理想政治”的想象性建构——在不触碰“孝”的核心原则、不撼动皇权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个体的智慧与胆识,在“孝”与“义”的缝隙中寻求正义的可能,让“孝治”不再是包庇恶行的借口,而是与公平正义相辅相成的政治伦理。这种建构,与关汉卿原著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却因“孝”的融入更具现实张力与人性温度。

元杂剧中的“包公戏”,本就是对元代社会“权豪势要横行” 的现实批判,关汉卿借包公之口,喊出“王法条条诛滥官” 的呐喊;而今川剧的改编,并未消解这份批判力度,反而以川剧生活化的表演特质,结合历史背景,让这份批判更具共情力——当李四、张珪等平民百姓在舞台上哭诉妻离子散之苦,当老旦演员以“如泣如诉”的唱腔传递绝望,观众既能感受到鲁斋郎借孝之名行特权之恶的荒谬,也能理解仁宗在孝治与民生之间的两难,更能共情包拯在尽孝与为民之间的挣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勾连,让作品超越了戏剧的范畴,不仅批判了封建时代的特权乱象,更引发当代观众对“规则与人情”“传统美德与社会公平”“特权现象”关系的深度思考。
二、从“铁面无私”到“纠结的刚正”,包公形象的人性化突破
在传统戏曲舞台上,包公往往是“神化”的符号:黑面、额间月牙、刚正不阿,仿佛天生没有犹豫与软弱。但川剧《智斩鲁斋郎》却大胆地撕开了这层“符号外衣”,如第五场“探访”与最终的“智铡”篇章中,着重刻画了包拯为难与纠结的情绪——刚正不阿的人也会为难,也会有各种纠结在他的思绪里。这段表演打破了观众对包公的固有认知:他不再是无所不能的正义机器,而是有血有肉的官员,要在皇权压力与百姓期盼之间权衡,要在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之间抉择。

这种“人性化重塑”,是对“包公符号 ”的深度挖掘。剧中包拯那句“贤侄,可否给叔父一个面子”的台词,曾被部分观众质疑“不符合包公形象”,但从学术视角看,这恰恰是作品的点睛之笔:它承认了包拯作为“朝堂官员”的身份局限性——他无法像民间传说中那样“铡刀一开,皇权不问”,只能在人际关系的缝隙中寻求解决之道。这种不完美的正义,比完美的神化更具现实说服力:它告诉观众,正义的实现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爽快,而是步步为营的坚持。
更值得关注的是,剧中女性角色的塑造,为“包公戏”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唱词“包青天也有你的半边天”,看似简单一句,却打破了传统公案戏中“女性仅为受害者”的刻板定位——它暗示着“正义”不仅是对男性权益的维护,也应包含对女性尊严的尊重。李母(彭春燕饰)的唱腔尤为典型:高亢的“亮音”中裹着温润,这种声腔特质,将母亲的坚韧与平民的不屈融为一体,让女性角色不再是推动剧情的工具人,而是承载民心的重要载体。这种改编,呼应了当代社会对性别平等的追求,让古典戏剧有了现代意识。

三、川剧的艺术突围,用川剧讲好中国故事
《智斩鲁斋郎》的成功,在于它守住了川剧的“根”,又扎下了新的“芽”。作品充分发挥了川剧“帮打唱”的声腔优势:净角(刘世虎饰包公)的唱腔浑厚圆润,配合“勾脸”与“功架”,将包公的伟岸形象立得扎实;“帮腔”的穿插则如画外音般,将观众的情绪引入剧情深处——当包公纠结时,帮腔的婉转传递出民心的期盼;当鲁斋郎嚣张时,弹戏的急促又烘托出正义的紧迫感。这种“声腔与情感”的高度融合,正是川剧“以声传情、以腔塑人”的精髓所在。
在叙事结构与舞美设计上,作品又展现了地方剧团的当代视野。全剧“抢亲、情深、巧救、夜抢、探访、请旨、智铡”七场戏,删繁就简,避免了传统戏曲“叙事拖沓”的弊端,以“鲁斋郎作恶—百姓受难—包公施计”的紧凑节奏,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舞美服装华丽精致,并非“经费堆砌”的炫技,而是以简约的布景(如朝堂的威严、民宅的破败)形成视觉对比,强化了权与民的矛盾冲突。这种“传统程式+现代审美”的融合,证明川剧无需迎合潮流而失本,只需找准定位而创新,便能在当代文艺主流行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遂宁市川剧团作为地方院团,虽无国家级院团的资源优势与流量IP加持,却凭借“四梁八柱”的整齐阵容及对川剧花脸声腔艺术的坚守,将古典公案戏《智斩鲁斋郎》演绎得“戏味浓郁、戏韵悠长”,这印证了川剧的生命力不在于复制经典,而在于以地方独特语言解读经典故事的当代价值,用演员扎实功力传递传统文化精神力量——正如剧中李母“亮得明晰,又透着点烟火气的暖”的唱腔,将大历史转化为小叙事,让观众在声腔与表演中感知传统文化与自身生活的紧密关联。当大幕落下、包公身影定格,从关汉卿元杂剧到如今川剧改编,斩鲁斋郎的故事能流传数百年,正因它触及对特权的反抗、对正义的渴望这一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而川剧的演绎更为此注入新的生命力,也让我们确信:传统不是束缚创新的枷锁,而是滋养创新的土壤;地方戏曲亦非小众喜好,而是能与当代观众对话、与现实社会共鸣的“活态文化”,因为它们讲述的不仅是过去的故事,更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正义与民心。
文章经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图片源自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