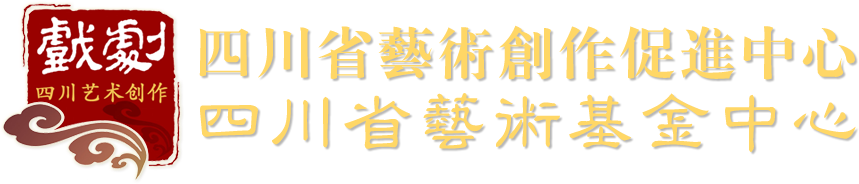
舞剧《山止川行》
——诸葛亮题材舞剧的艺术解构
林晓婧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历史与文学中,诸葛亮早已成为一个高度符号化的形象——智慧的化身、忠臣的典范,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情英雄。将这样一位人物搬上舞台,编创者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超越既有的叙事框架,找到一种属于舞蹈本体语言的美学路径。《山止川行》选择了以诗入舞,以意代叙。剧名即是一种美学宣言:以“山”象征人格的定力与理想的崇高,以“止”体现静守之志与生命的回响,以“川”隐喻时间的流逝与命运的进程,以“行”展现个体在静与动之间的跋涉、求索与精神轨迹。这部剧因而不仅仅是对诸葛亮生平的再现,更是以他为载体,展开一场关于责任、自由、生命意义与精神延续的哲学思辨。
一、山——理想的奠基与悲壮的底色
大幕开启,并非喧嚣的三顾场景,而是一派沉静、内省的氛围。红色与白色的碰撞,构成了第一幕的视觉基调。刘备的红,是炎汉的血脉,是求贤若渴的炽热,是乱世创业的激情;诸葛亮的白,是隆中的云雾,是淡泊明志的纯净,是超然物外的身份。这两种色彩的对话,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诸葛亮一生无法摆脱的基调:个人宁静与天下苍生的巨大矛盾。

古琴的出现,是第一个,也是贯穿全剧的核心符号。它在此处,不仅是道具,更是角色。当刘备与诸葛亮的双人舞在古琴幽咽的泛音与钢琴沉厚的柱式和弦中展开时,观众“听”到的是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对话。男性的双人舞,充满了力量的托举、智慧的碰撞与信念的交付。舞蹈动作设计刚劲而充满张力,每一次旋转、每一次支撑,都是意志与理想的对接。此时主题旋律盘旋而下,最终落于一个悬而未决的小调属音上,像一句命运的低语,在最为意气风发的时刻,已然播下了悲壮的种子。这乐句并非单纯的哀伤,而是一种深沉的、洞观历史循环的悲悯,预示着这条“出世”之路,终将通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终点。
“修蜀道,筑剑阁,运筹帷幄蜀困兴”的宏大叙事,在舞台上转化为一股原始、粗犷的生命洪流。绿色服饰的群舞演员,以充满力量感且看似“不规整”的动作,在不协和音响、强劲打击乐与人声号子的交织中,演绎着创业维艰。这恰是编导的深意:秩序诞生于混沌,“山”的巍峨,正建立在这片充满野性张力的广阔地基之上。
然而,孤峰注定要承受最猛烈的风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痛失街亭,挥泪斩马谡”的悲剧,并未以写实场面呈现,而是通过舞台节奏的骤变来外化。菱形光区、穿梭的蓝色身影、融入“醉拳”韵味的舞步,以及突如其来的电声音效,共同构成一个焦虑、断裂的时空,映射出诸葛亮内心秩序遭遇的致命一击。
也正是在这裂痕之中,孤峰的坚韧与智慧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一座空城,古琴声悠,妙退司马懿大军”的经典桥段,被升华至本幕巅峰。舞台上,诸葛亮与古琴再次成为焦点。此刻,琴不再是礼器,而化作了唯一的武器。这段舞,是诸葛亮一生“山”之意志的浓缩体现:任它风狂雨骤,我自岿然屹立,以内心的绝对平静,对抗外在的百万雄兵。这不仅是妙计,更是一种孤绝的、美学意义上的存在姿态,将第一幕的“悲壮”底色,推向了令人心潮澎湃的崇高之境。
二、止——静守之志与生命的回响
若说第一幕“山”勾勒出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的精神风骨,第二幕“止”则从容展开其身为“人”的丰富层次。这一幕以情感的细腻与民生的温度,构建起一幅动静相生、守中有进的生命图景。
幕启于温情。诸葛亮与妻子的双人舞在风铃声与柔和的钢琴弦乐中展开。女声吟唱如耳语般营造出温馨氛围,只有依偎的剪影与交织的眼神,于细微处见深情。这份“静守”,并非退缩,而是人格深处的情感定力。当古琴声再度响起,象征着国事对个人生活的召唤,音乐上形成“家”与“国”的对话,外化出他在情感羁绊与天下责任间的复杂心绪。妻子为其整饬衣冠的细微动作,道尽“舍小家”的克制与“顾大家”的持重,静守于此,升华为一种清醒的责任担当。
场景流转,舞台色调转为象征生机的绿色。木牛流马的巧妙设计,不仅是军事智慧的闪现,更是治国方略的缩影。随之而来的农耕群舞,秩序井然,勾勒出“重视农耕安蜀地”的安居画卷。诸葛亮其“静守”的理想,在此具体化为“仁政”的实践。他静守的,非一己之安,而是这一派生机勃勃的烟火人间。
“止”的意境,在《春归引》的深情演绎中臻于圆满。姜维等人的出现,象征着事业与精神的后继有人;而“北伐一去路遥遥”的远征前景,与“春归引”的温暖意象,构成一种深远的张力。静守,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长远的行进。这一幕的“止”,因而成为全剧气韵流转的关键——它既是情感的归依,也是力量的积蓄,更是诸葛亮在历史激流中主动选择的精神锚点。

三、川——北伐的无望与命运的呼啸
“川”,在此既是时间的隐喻,也是命运的具象。若说“山”是诸葛亮立身的根基,那么“川”便是那环绕他、推动他、最终将其包容的永恒之流。这一幕以愈发湍急的节奏,展现其晚年北伐征程中,个体意志在历史长河与命运进程前的激荡、挣扎与深沉悲怆。
幕启时,一束追光刺破黑暗,金乌的独舞拉开命运帷幕。舞者以扭曲、挣扎的舞姿演绎着“金乌鸣,玄机明”的谶语,每一次振翅都仿佛在挣脱无形的枷锁。这段充满张力的独舞,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天命与人事的剧烈冲突。当金乌最终力竭倒地,舞台后方渐渐显现出“长星坠营”的悲壮场景——将士们素缟如雪,动作滞重如逆水行舟。诸葛亮穿梭其间,每一次向前的冲刺都被无形的巨力推回,这种视觉上的阻滞感让观众切身感受到“天不助汉”的无奈。

随着剧情推进,舞台色调骤然分裂为红绿对峙。在戏曲锣鼓与不协和弦乐制造的湍流声中,观众目睹诸葛亮与暗色群舞的周旋。特别当司马懿女装避战的场面出现时,这种视觉反差让时间站在对手一侧的讽刺感愈发强烈。观众能清晰感受到,诸葛亮所有的“运筹帷幄”在时间这位终极对手面前的无力。
最令人动容的是落幕处的转变:当北伐烽火渐渐熄灭,诸葛亮的身影在象征时间洪流的舞台意象前逐渐凝滞。这个从激烈挣扎到坦然静默的过程,让观众得以窥见一个智者与命运的和解。我们仿佛与他一同领悟:个人的意志终将汇入历史长河,而精神的价值正在于这“川行”的过程本身。
至此,观众的体验已从观看一段历史,转为聆听一个灵魂在命运长河中的深沉回响。金乌的再次现身,如同一个永恒的史诗注脚,它与诸葛亮的遥遥对望,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也为最终的超越埋下了深刻的伏笔。
四、行——陨落与传承
“功成八阵图,遗坠五丈原”最后一“行”,是生命的终章,更是精神的远征。当“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宿命如期而至,“行”的含义得以最终彰显:它是步履的终结,亦是灵魂的启程。
舞台以极具张力的盾牌舞开场。急促的鼓点如命运倒计时,舞者手持盾牌,以严谨的阵法变换勾勒出最后的智慧防线。这既是“死诸葛走生仲达”的谋略再现,更是智慧与命运的最后博弈。盾牌相击的金属声与渐起的风雨声交织,预示着生命终将来临。
在阵法散去的刹那,盏盏孔明灯冉冉升起,温暖的光晕中,“羽化登仙”的东方美学意境取代了死亡的阴霾。低音提琴以深沉的音色铺陈追忆的基调,随后第一幕的主旋律再度响起。经过生命的淬炼,相同的旋律已褪去青涩,镀上了宏大而宁静的色彩。这音乐上的首尾呼应,完美诠释了“山止川行”的深刻内涵:个体生命的“山”虽有倾颓之时,但其精神却已汇入文明的“川流”,永续不绝。
全剧在“明灯陨落,羽化而登仙”的意境中落幕,完成了一场从有限生命到无限精神的伟大“行”旅。

舞剧《山止川行》的成功,在于它完成了一次“翻译”工作:它将一段厚重的历史,翻译成了跨越国界与时代的人类共通情感;将文字翻译成肢体的诗篇;将个人的命运悲剧,翻译成关于精神永恒的哲学思考。它让我们看到,诸葛亮最大的魅力,或许不在于他的算无遗策,而在于他在明知“天命”不可为下的“人事”为之,在于那种极致的、悲剧性的理想主义光辉。
这部剧不仅是对一位千古名相的致敬,更是对当下时代每一个负重“行走”的灵魂的深切叩问。在功利的喧嚣与易碎的理想之间,我们是否还能听见内心深处那声《归去来兮》的呼唤?是否还能为了心中的“道”,而选择做一座孤独却坚定的“山”?《山止川行》给出了答案。
文章经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图片源自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舞剧《山止川行》
——诸葛亮题材舞剧的艺术解构
林晓婧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历史与文学中,诸葛亮早已成为一个高度符号化的形象——智慧的化身、忠臣的典范,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情英雄。将这样一位人物搬上舞台,编创者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超越既有的叙事框架,找到一种属于舞蹈本体语言的美学路径。《山止川行》选择了以诗入舞,以意代叙。剧名即是一种美学宣言:以“山”象征人格的定力与理想的崇高,以“止”体现静守之志与生命的回响,以“川”隐喻时间的流逝与命运的进程,以“行”展现个体在静与动之间的跋涉、求索与精神轨迹。这部剧因而不仅仅是对诸葛亮生平的再现,更是以他为载体,展开一场关于责任、自由、生命意义与精神延续的哲学思辨。
一、山——理想的奠基与悲壮的底色
大幕开启,并非喧嚣的三顾场景,而是一派沉静、内省的氛围。红色与白色的碰撞,构成了第一幕的视觉基调。刘备的红,是炎汉的血脉,是求贤若渴的炽热,是乱世创业的激情;诸葛亮的白,是隆中的云雾,是淡泊明志的纯净,是超然物外的身份。这两种色彩的对话,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诸葛亮一生无法摆脱的基调:个人宁静与天下苍生的巨大矛盾。

古琴的出现,是第一个,也是贯穿全剧的核心符号。它在此处,不仅是道具,更是角色。当刘备与诸葛亮的双人舞在古琴幽咽的泛音与钢琴沉厚的柱式和弦中展开时,观众“听”到的是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对话。男性的双人舞,充满了力量的托举、智慧的碰撞与信念的交付。舞蹈动作设计刚劲而充满张力,每一次旋转、每一次支撑,都是意志与理想的对接。此时主题旋律盘旋而下,最终落于一个悬而未决的小调属音上,像一句命运的低语,在最为意气风发的时刻,已然播下了悲壮的种子。这乐句并非单纯的哀伤,而是一种深沉的、洞观历史循环的悲悯,预示着这条“出世”之路,终将通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终点。
“修蜀道,筑剑阁,运筹帷幄蜀困兴”的宏大叙事,在舞台上转化为一股原始、粗犷的生命洪流。绿色服饰的群舞演员,以充满力量感且看似“不规整”的动作,在不协和音响、强劲打击乐与人声号子的交织中,演绎着创业维艰。这恰是编导的深意:秩序诞生于混沌,“山”的巍峨,正建立在这片充满野性张力的广阔地基之上。
然而,孤峰注定要承受最猛烈的风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痛失街亭,挥泪斩马谡”的悲剧,并未以写实场面呈现,而是通过舞台节奏的骤变来外化。菱形光区、穿梭的蓝色身影、融入“醉拳”韵味的舞步,以及突如其来的电声音效,共同构成一个焦虑、断裂的时空,映射出诸葛亮内心秩序遭遇的致命一击。
也正是在这裂痕之中,孤峰的坚韧与智慧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一座空城,古琴声悠,妙退司马懿大军”的经典桥段,被升华至本幕巅峰。舞台上,诸葛亮与古琴再次成为焦点。此刻,琴不再是礼器,而化作了唯一的武器。这段舞,是诸葛亮一生“山”之意志的浓缩体现:任它风狂雨骤,我自岿然屹立,以内心的绝对平静,对抗外在的百万雄兵。这不仅是妙计,更是一种孤绝的、美学意义上的存在姿态,将第一幕的“悲壮”底色,推向了令人心潮澎湃的崇高之境。
二、止——静守之志与生命的回响
若说第一幕“山”勾勒出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的精神风骨,第二幕“止”则从容展开其身为“人”的丰富层次。这一幕以情感的细腻与民生的温度,构建起一幅动静相生、守中有进的生命图景。
幕启于温情。诸葛亮与妻子的双人舞在风铃声与柔和的钢琴弦乐中展开。女声吟唱如耳语般营造出温馨氛围,只有依偎的剪影与交织的眼神,于细微处见深情。这份“静守”,并非退缩,而是人格深处的情感定力。当古琴声再度响起,象征着国事对个人生活的召唤,音乐上形成“家”与“国”的对话,外化出他在情感羁绊与天下责任间的复杂心绪。妻子为其整饬衣冠的细微动作,道尽“舍小家”的克制与“顾大家”的持重,静守于此,升华为一种清醒的责任担当。
场景流转,舞台色调转为象征生机的绿色。木牛流马的巧妙设计,不仅是军事智慧的闪现,更是治国方略的缩影。随之而来的农耕群舞,秩序井然,勾勒出“重视农耕安蜀地”的安居画卷。诸葛亮其“静守”的理想,在此具体化为“仁政”的实践。他静守的,非一己之安,而是这一派生机勃勃的烟火人间。
“止”的意境,在《春归引》的深情演绎中臻于圆满。姜维等人的出现,象征着事业与精神的后继有人;而“北伐一去路遥遥”的远征前景,与“春归引”的温暖意象,构成一种深远的张力。静守,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长远的行进。这一幕的“止”,因而成为全剧气韵流转的关键——它既是情感的归依,也是力量的积蓄,更是诸葛亮在历史激流中主动选择的精神锚点。

三、川——北伐的无望与命运的呼啸
“川”,在此既是时间的隐喻,也是命运的具象。若说“山”是诸葛亮立身的根基,那么“川”便是那环绕他、推动他、最终将其包容的永恒之流。这一幕以愈发湍急的节奏,展现其晚年北伐征程中,个体意志在历史长河与命运进程前的激荡、挣扎与深沉悲怆。
幕启时,一束追光刺破黑暗,金乌的独舞拉开命运帷幕。舞者以扭曲、挣扎的舞姿演绎着“金乌鸣,玄机明”的谶语,每一次振翅都仿佛在挣脱无形的枷锁。这段充满张力的独舞,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天命与人事的剧烈冲突。当金乌最终力竭倒地,舞台后方渐渐显现出“长星坠营”的悲壮场景——将士们素缟如雪,动作滞重如逆水行舟。诸葛亮穿梭其间,每一次向前的冲刺都被无形的巨力推回,这种视觉上的阻滞感让观众切身感受到“天不助汉”的无奈。

随着剧情推进,舞台色调骤然分裂为红绿对峙。在戏曲锣鼓与不协和弦乐制造的湍流声中,观众目睹诸葛亮与暗色群舞的周旋。特别当司马懿女装避战的场面出现时,这种视觉反差让时间站在对手一侧的讽刺感愈发强烈。观众能清晰感受到,诸葛亮所有的“运筹帷幄”在时间这位终极对手面前的无力。
最令人动容的是落幕处的转变:当北伐烽火渐渐熄灭,诸葛亮的身影在象征时间洪流的舞台意象前逐渐凝滞。这个从激烈挣扎到坦然静默的过程,让观众得以窥见一个智者与命运的和解。我们仿佛与他一同领悟:个人的意志终将汇入历史长河,而精神的价值正在于这“川行”的过程本身。
至此,观众的体验已从观看一段历史,转为聆听一个灵魂在命运长河中的深沉回响。金乌的再次现身,如同一个永恒的史诗注脚,它与诸葛亮的遥遥对望,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也为最终的超越埋下了深刻的伏笔。
四、行——陨落与传承
“功成八阵图,遗坠五丈原”最后一“行”,是生命的终章,更是精神的远征。当“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宿命如期而至,“行”的含义得以最终彰显:它是步履的终结,亦是灵魂的启程。
舞台以极具张力的盾牌舞开场。急促的鼓点如命运倒计时,舞者手持盾牌,以严谨的阵法变换勾勒出最后的智慧防线。这既是“死诸葛走生仲达”的谋略再现,更是智慧与命运的最后博弈。盾牌相击的金属声与渐起的风雨声交织,预示着生命终将来临。
在阵法散去的刹那,盏盏孔明灯冉冉升起,温暖的光晕中,“羽化登仙”的东方美学意境取代了死亡的阴霾。低音提琴以深沉的音色铺陈追忆的基调,随后第一幕的主旋律再度响起。经过生命的淬炼,相同的旋律已褪去青涩,镀上了宏大而宁静的色彩。这音乐上的首尾呼应,完美诠释了“山止川行”的深刻内涵:个体生命的“山”虽有倾颓之时,但其精神却已汇入文明的“川流”,永续不绝。
全剧在“明灯陨落,羽化而登仙”的意境中落幕,完成了一场从有限生命到无限精神的伟大“行”旅。

舞剧《山止川行》的成功,在于它完成了一次“翻译”工作:它将一段厚重的历史,翻译成了跨越国界与时代的人类共通情感;将文字翻译成肢体的诗篇;将个人的命运悲剧,翻译成关于精神永恒的哲学思考。它让我们看到,诸葛亮最大的魅力,或许不在于他的算无遗策,而在于他在明知“天命”不可为下的“人事”为之,在于那种极致的、悲剧性的理想主义光辉。
这部剧不仅是对一位千古名相的致敬,更是对当下时代每一个负重“行走”的灵魂的深切叩问。在功利的喧嚣与易碎的理想之间,我们是否还能听见内心深处那声《归去来兮》的呼唤?是否还能为了心中的“道”,而选择做一座孤独却坚定的“山”?《山止川行》给出了答案。
文章经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图片源自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