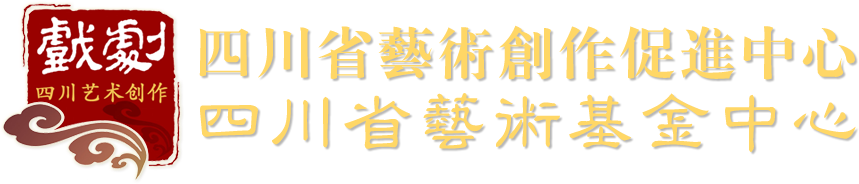
成败皆是戏,起落总关情
——评《梦回东坡》人物塑造与情节处理
李 湘
重庆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大四在读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此为苏轼被贬黄州之后,一次与友人聚会醉归遇雨抒怀之作。那时的他已过不惑之年,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川剧《梦回东坡》借用此句收官,可谓自成妙用、画龙点睛,既区别于同题材的其他戏剧样式,历久弥新、别开生面;又精准捕捉主人公性格的核心特质,体现了川剧人物塑造细腻、生活气息浓郁的艺术特点。
能在浩若烟海的文史典籍中留其名者不胜枚举,他们当中或以书画见长者,如王羲之、郑板桥等;或以诗歌誉满天下者,如屈原、陶渊明等;或以文章流传千古者,如王勃、范仲淹……在这些文人墨客中,诗、词、文章、书、画、人品俱佳的苏轼无疑是一位“六边形战士”,不仅备受后世文人学者的崇敬,更因元代文人的现实境遇与苏轼相似,以苏轼为题材的元杂剧通过民间艺人的演绎,在市井之中也广为流传。可以说,自古典戏曲诞生之日起,苏东坡就一直是各剧种竞相塑造和演绎的流量角色。单看近十年,舞台上就涌现了多部以苏东坡为主题的剧目,如《东坡海南》《苏东坡》《海上东坡》《诗艺东坡》《苏堤春晓》《大江东去》等,涵盖了舞剧、话剧、现代舞诗剧、音乐剧等多种体裁。然而,面对本土最有辨识度的历史文化名人,丰富的历史资料、民间传说堆叠在那里,倘若没有一部纪念先贤的作品,这是所有川剧从业者的遗憾。

在剧作上,《梦回东坡》的编剧回避了苏轼被贬的具体政治原因,没有放大宋代新旧两党之争,强调个人成长与精神转变更能引起现代观众的共鸣,而且将焦点放在政治议题上也可能分散观众对苏轼个人情感与精神世界的关注。《梦回东坡》的结构是用苏轼的梦境串联起八个片段,展现他不同时期的生活横截面,每段独立完整又相互呼应,都有自成逻辑的情绪高潮,共同构建起苏轼的人物形象。呈块状的叙事结构让角色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自由跳跃,基于这个叙事特点,苏轼被贬到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时个人情感与人际关系的戏剧化冲突。
无论剧中还是生活中,面对不同的人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这就是所谓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基于此,在人物塑造上,《梦回东坡》选择从苏东坡的人际网络出发,全方位地展现苏东坡的复杂性格与多维面貌。比如,剧中苏东坡在梦中与双亲重逢的场景,用家庭的温情中和官场的肃杀气氛,还传达了一个普遍真理:在父母心中,无论孩子年龄多大、成就如何,永远都是需要呵护与疼爱的孩子,便于观众与主人公共情。这样的设定,在戏剧的开场尤为重要,如果观众对人物的戏剧动作不认同,随后便会引发一连串的排斥和抵触情绪。同时,在爱情叙事的选择上,该剧并未全面铺陈苏轼三段情感生活的全貌,特别是避开了最知名的伴侣王弗,而是将焦点集中在了他与王闰之的第二段婚姻上。王闰之与苏轼共同生活的年岁正是苏轼在官场上的消沉时期,二人互帮互助的亲密关系使观众更深层次地理解苏轼作为丈夫的一面。
此外,按照一般逻辑推测,王闰之作为目不识丁的村妇,与满腹经纶的苏轼,两人的精神世界应处于截然不同的维度,难以产生交集。因此,如何精心挑选合适的情节,规避这些可能导致婚姻裂痕的隐患,显得尤为重要。本剧对此的处理堪称教科书:由于乌台诗案给王闰之留下了心理阴影,她深怕丈夫苏轼会再次陷入类似的困境,于是出于保护之心,将丈夫的诗稿付之一炬。这一举动,若按世俗眼光来看,或许会被视作一种不明智的“败家行为”,极有可能将夫妻关系推向深渊。然而,王闰之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后,迅速发挥聪明睿智,在市集上四处奔走,以钱财为交换条件,鼓励百姓们背诵并记录下丈夫的诗词,最终成功集满一匣子诗稿完璧归苏,从而将一场风波消弭于无形。这样的情节构思既维护了两人情感的根基,绕开了婚姻中常见的误解与隔阂,又展现了王闰之独有的个人魅力。即使她未曾受过诗书教化,但与生俱来的聪慧与敏锐,恰恰是成就她与才子苏轼和谐共处的关键所在,证明了真正的伴侣并不受限于学识的高低,而在于心灵的契合与相互的理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剧把乌台诗案这一对苏轼影响最大的事件的处理。从《梦回东坡》的叙事脉络来审视,该剧仿佛是苏东坡在向双亲细述平生。将乌台诗案放倒数第二场的处理,展现了中国人对父母“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情感倾向,也真实地呈现了苏轼在严酷刑罚下的内心挣扎与妥协。在父母眼中,他们的儿子即使身处逆境,也定当坚韧不屈,绝不认罪。然而,即使是凡人如苏东坡,也难以抵挡认罪的“诱惑”,毕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认罪亦非难事。该剧并未将苏东坡塑造为一个完美的神祇,而是用人物的缺点刻画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因为,真正的艺术并非在于塑造无瑕的英雄。
虽然这场戏在人物塑造方面是优秀的,但剧情的连贯性存在一定问题。第六场东坡失妻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紧接着的第七场乌台诗案,在缺少过渡且观众已经知道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最终无恙的情况下,展现苏东坡在重刑之下被迫认罪的过程。这种突然从高度情绪化的悲伤中直接跳进一个紧张事件的安排,使观众难以迅速关心苏东坡的个人命运,以至于这场本身很优秀的戏在整体叙事中显得有些拖沓。

相较于2023年的演出版本,2024年在第六届川剧节暨四川省第二届川剧汇演上呈现的《梦回东坡》进行了调整:去除了苏东坡在海南与昔日对手章惇的交集,新增了苏轼因八位老兵“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壮志情怀而创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情节。这一增删的考量可能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苏东坡的胸怀与乐观已充分展现,与章惇关系的转变对丰富人物形象的作用有限。二是为更聚焦苏东坡与四川的联系及其特殊地域背景下的生活经历,有意减少了其他人生阶段的篇幅。至于新增的八位老兵戏份,不仅直接关联到苏轼的创作灵感,还反映了他对历史英雄的敬仰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思考。《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融入,并非简单地与老兵对话或直抒胸臆地讨论国事,而是通过诗意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画卷,让观众在感受苏轼文学魅力的同时,也能体会到他面对人生坎坷时的豁达与哲理。剧作的结尾,依然不忘重申苏轼对于人生挫折的独特见解与感悟,为整部剧作画上了一个圆满而富有深意的句号。
苏东坡在剧中的人生历程,以其非凡的智慧与无畏的勇气震撼着观众,尤其是逆境中的乐观与豁达,成为了激励现代人心灵的精神力量,某种程度上映射出现代观众的价值取向。《梦回东坡》在保留川剧独特韵味的同时,大胆采用更为现代的叙事手法,贴近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从观众现场的热情反馈来看,这一创新尝试无疑是成功的,为同行树立了良好的典范。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对时代审美的不断探索与契合,任何艺术形式若故步自封、拒绝变革,终将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梦回东坡》的成功实践提醒我们,只有勇于尝试、积极创新,才能让艺术之树常青,走得更远。
本文经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
成败皆是戏,起落总关情
——评《梦回东坡》人物塑造与情节处理
李 湘
重庆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大四在读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此为苏轼被贬黄州之后,一次与友人聚会醉归遇雨抒怀之作。那时的他已过不惑之年,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川剧《梦回东坡》借用此句收官,可谓自成妙用、画龙点睛,既区别于同题材的其他戏剧样式,历久弥新、别开生面;又精准捕捉主人公性格的核心特质,体现了川剧人物塑造细腻、生活气息浓郁的艺术特点。
能在浩若烟海的文史典籍中留其名者不胜枚举,他们当中或以书画见长者,如王羲之、郑板桥等;或以诗歌誉满天下者,如屈原、陶渊明等;或以文章流传千古者,如王勃、范仲淹……在这些文人墨客中,诗、词、文章、书、画、人品俱佳的苏轼无疑是一位“六边形战士”,不仅备受后世文人学者的崇敬,更因元代文人的现实境遇与苏轼相似,以苏轼为题材的元杂剧通过民间艺人的演绎,在市井之中也广为流传。可以说,自古典戏曲诞生之日起,苏东坡就一直是各剧种竞相塑造和演绎的流量角色。单看近十年,舞台上就涌现了多部以苏东坡为主题的剧目,如《东坡海南》《苏东坡》《海上东坡》《诗艺东坡》《苏堤春晓》《大江东去》等,涵盖了舞剧、话剧、现代舞诗剧、音乐剧等多种体裁。然而,面对本土最有辨识度的历史文化名人,丰富的历史资料、民间传说堆叠在那里,倘若没有一部纪念先贤的作品,这是所有川剧从业者的遗憾。

在剧作上,《梦回东坡》的编剧回避了苏轼被贬的具体政治原因,没有放大宋代新旧两党之争,强调个人成长与精神转变更能引起现代观众的共鸣,而且将焦点放在政治议题上也可能分散观众对苏轼个人情感与精神世界的关注。《梦回东坡》的结构是用苏轼的梦境串联起八个片段,展现他不同时期的生活横截面,每段独立完整又相互呼应,都有自成逻辑的情绪高潮,共同构建起苏轼的人物形象。呈块状的叙事结构让角色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自由跳跃,基于这个叙事特点,苏轼被贬到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时个人情感与人际关系的戏剧化冲突。
无论剧中还是生活中,面对不同的人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这就是所谓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基于此,在人物塑造上,《梦回东坡》选择从苏东坡的人际网络出发,全方位地展现苏东坡的复杂性格与多维面貌。比如,剧中苏东坡在梦中与双亲重逢的场景,用家庭的温情中和官场的肃杀气氛,还传达了一个普遍真理:在父母心中,无论孩子年龄多大、成就如何,永远都是需要呵护与疼爱的孩子,便于观众与主人公共情。这样的设定,在戏剧的开场尤为重要,如果观众对人物的戏剧动作不认同,随后便会引发一连串的排斥和抵触情绪。同时,在爱情叙事的选择上,该剧并未全面铺陈苏轼三段情感生活的全貌,特别是避开了最知名的伴侣王弗,而是将焦点集中在了他与王闰之的第二段婚姻上。王闰之与苏轼共同生活的年岁正是苏轼在官场上的消沉时期,二人互帮互助的亲密关系使观众更深层次地理解苏轼作为丈夫的一面。
此外,按照一般逻辑推测,王闰之作为目不识丁的村妇,与满腹经纶的苏轼,两人的精神世界应处于截然不同的维度,难以产生交集。因此,如何精心挑选合适的情节,规避这些可能导致婚姻裂痕的隐患,显得尤为重要。本剧对此的处理堪称教科书:由于乌台诗案给王闰之留下了心理阴影,她深怕丈夫苏轼会再次陷入类似的困境,于是出于保护之心,将丈夫的诗稿付之一炬。这一举动,若按世俗眼光来看,或许会被视作一种不明智的“败家行为”,极有可能将夫妻关系推向深渊。然而,王闰之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后,迅速发挥聪明睿智,在市集上四处奔走,以钱财为交换条件,鼓励百姓们背诵并记录下丈夫的诗词,最终成功集满一匣子诗稿完璧归苏,从而将一场风波消弭于无形。这样的情节构思既维护了两人情感的根基,绕开了婚姻中常见的误解与隔阂,又展现了王闰之独有的个人魅力。即使她未曾受过诗书教化,但与生俱来的聪慧与敏锐,恰恰是成就她与才子苏轼和谐共处的关键所在,证明了真正的伴侣并不受限于学识的高低,而在于心灵的契合与相互的理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剧把乌台诗案这一对苏轼影响最大的事件的处理。从《梦回东坡》的叙事脉络来审视,该剧仿佛是苏东坡在向双亲细述平生。将乌台诗案放倒数第二场的处理,展现了中国人对父母“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情感倾向,也真实地呈现了苏轼在严酷刑罚下的内心挣扎与妥协。在父母眼中,他们的儿子即使身处逆境,也定当坚韧不屈,绝不认罪。然而,即使是凡人如苏东坡,也难以抵挡认罪的“诱惑”,毕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认罪亦非难事。该剧并未将苏东坡塑造为一个完美的神祇,而是用人物的缺点刻画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因为,真正的艺术并非在于塑造无瑕的英雄。
虽然这场戏在人物塑造方面是优秀的,但剧情的连贯性存在一定问题。第六场东坡失妻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紧接着的第七场乌台诗案,在缺少过渡且观众已经知道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最终无恙的情况下,展现苏东坡在重刑之下被迫认罪的过程。这种突然从高度情绪化的悲伤中直接跳进一个紧张事件的安排,使观众难以迅速关心苏东坡的个人命运,以至于这场本身很优秀的戏在整体叙事中显得有些拖沓。

相较于2023年的演出版本,2024年在第六届川剧节暨四川省第二届川剧汇演上呈现的《梦回东坡》进行了调整:去除了苏东坡在海南与昔日对手章惇的交集,新增了苏轼因八位老兵“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壮志情怀而创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情节。这一增删的考量可能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苏东坡的胸怀与乐观已充分展现,与章惇关系的转变对丰富人物形象的作用有限。二是为更聚焦苏东坡与四川的联系及其特殊地域背景下的生活经历,有意减少了其他人生阶段的篇幅。至于新增的八位老兵戏份,不仅直接关联到苏轼的创作灵感,还反映了他对历史英雄的敬仰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思考。《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融入,并非简单地与老兵对话或直抒胸臆地讨论国事,而是通过诗意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画卷,让观众在感受苏轼文学魅力的同时,也能体会到他面对人生坎坷时的豁达与哲理。剧作的结尾,依然不忘重申苏轼对于人生挫折的独特见解与感悟,为整部剧作画上了一个圆满而富有深意的句号。
苏东坡在剧中的人生历程,以其非凡的智慧与无畏的勇气震撼着观众,尤其是逆境中的乐观与豁达,成为了激励现代人心灵的精神力量,某种程度上映射出现代观众的价值取向。《梦回东坡》在保留川剧独特韵味的同时,大胆采用更为现代的叙事手法,贴近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从观众现场的热情反馈来看,这一创新尝试无疑是成功的,为同行树立了良好的典范。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对时代审美的不断探索与契合,任何艺术形式若故步自封、拒绝变革,终将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梦回东坡》的成功实践提醒我们,只有勇于尝试、积极创新,才能让艺术之树常青,走得更远。
本文经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950号